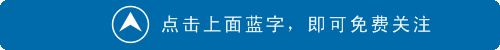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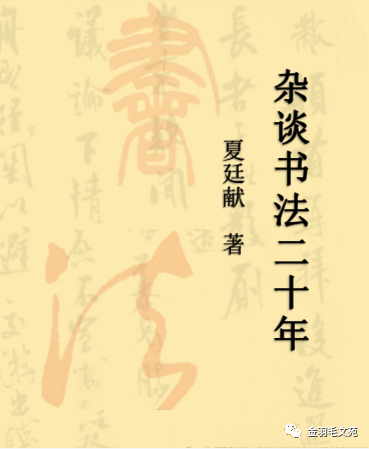
《杂谈书法二十年》
这是作者从1999年到2019年发表的书法评论文章汇编;是一部从普通读者角度辩证论述书法知识的“通俗读本”。全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涉猎到书法的基本理论、毛笔形成、基本笔法、骨文来历、汉字特征、结字技巧、草书格局、章法营造、法帖分析、书法鉴赏、书法命运、先贤经验、自身体会等。提出了诸如“超长画”“超大字”“神布局”“使用‘黑体’”“接纳‘饰书’”“书法精神”“书作‘三品级’”等新概念和新观点;记录了向当代22位书法家请教学习、采访交流的情况。是作者20年间对中国书法艺术观察与思考的“文字足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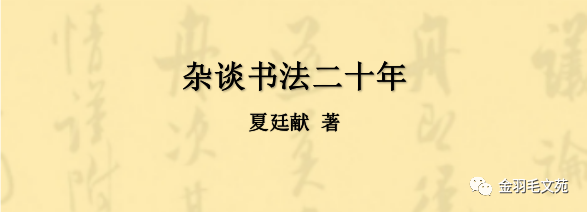
“生物”“事物”,处于“自然形态”时,往往发育发展得挺好。例如“国宝”大熊猫,人们没有发现之前,是何等的自在惬意。“人为因素”一介入,生态遭到破坏,便面临衰落乃至灭绝的危险。书法艺术“国宝”,也是这样。在没有明显的“人为因素”介入之前,出过多少大家啊!《书法导报》曾经列举了近千年的50名大师,还不包括本世纪的书法大家毛泽东。而自从有了“组织”、“职称”、“书展”、“评委”“会议”、尤其是“孔方兄”等“人为因素”“干预”之后,公认的“大家”倒反而很难出来了。何也?其中的“论争”,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什么“主义”、“观念”、“主张”、“流派”、“学派” 、“模式”,不一而足。南北书家“打”得不可开交,说得不明不白。普通书者虽然感到不胜其烦,但又不敢明说,怕人家嘲笑自己眼光浅水平低,没有看见“皇帝的新衣”。但书法是大众艺术,不是哪一部分人的专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谁都可以“说三道四”“评头品足”一番,只不过有的可以公开发表,影响“麾下”的群体。有的只能私下说说罢了,谁也影响不到。这里,笔者也想模仿一下书法大家,同普通书者来一个“对话”,说说书坛的“时尚言行”,一时找不到对话者,只好先同编辑说说。能不能发表出来同普通书者交流,那就看编辑先生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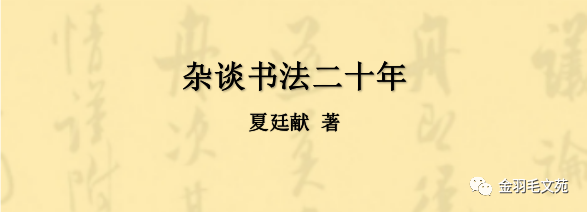
书法有“时代性”,一点不错。说不说,论不论,原本就是这样。在书法领域,对“时代性”问题,有人愿意“关注”,有人不愿意刻意“关注”,这些都是正常的,应当允许的。然而,有的书家动不动就把“时代要求”搬出来,认为“关注”时代,才是有“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反之呢,那就是没有。而且,还要求“以自己的创作与思考和时代衔接”,要找到“表现时代”的“衔接点”“模式”“方式”“主题”“语言”“角度”“道路”等等。乖乖,明明就是一个“写字”问题,说到了“玄而又玄”的“高度”上,还说“有人能走通”,“是对时代的很大贡献”。书法有“时代性”,但不一定要赋予它太重的时代“责任”和“使命”,它也承载不起。何况,“时代”,到底设定多长时间?50年?100年?300年?
一部书法史已经证明,50年,100年,根本不能做为“记量单位”。南宋诗人陆游工书法,在《学书》诗中写道: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他老人家是以500年为“单位”来衡量书法作品的。更何况,“时代”基本上是个政治概念,100年间,可以转换两三个“朝代”。50年,也可称为两三个“时代”,其“中心内容”也各不相同,“衔接”哪个时代好?如何进行“衔接”?“存在决定意识”“笔墨当随时代”,哪个时代的人写的字,自然就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想不带都办不到。所以这才有:汉人尚气,魏晋尚韵,南北朝尚神,隋唐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明人尚趣,清人尚朴之说,而且,这些“说”,也都是后人“总结”的,当时的人并没有说自己崇“尚”什么。因此,笔者以为,“时代性”问题,不要过份强调,少数专家谈谈可以,咱们普通书法爱好者,还是埋头练自己的字,无论怎样写,写什么——写古诗,还是写现代白话,既不会“跑”回古代去,更不会“飞”到未来去,一定是现“时代”的字。500年后,有人看到你的墨迹,也一定会说,这是20——21世纪之交的字,而不会说是秦始皇时代的字,更不会说是2500年的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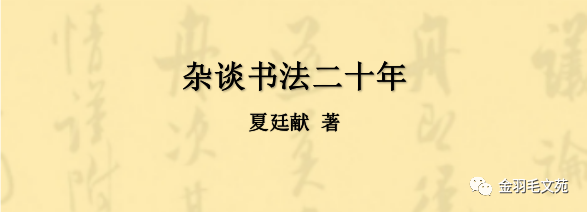
对书法提出“时代要求”的人,往往还会提出“西方文化”,似乎不这么说,不够“时代”。这些肩负着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先行者们,站在很高的时间“层面”上说,要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碰撞”中,找到“融合”的“衔接点”,要有敢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魄力与能力。如果不这样做,则似乎“谈创作、谈学术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些话很宏观,也很对。但对普通书者来说,则显得很“玄”,有点虚无飘渺之感。寻找“衔接点”的先行者们,至今也还没有找到被公认的“突破点”。一些在“形式”上的所谓“尝试”,圈内人自认“含金量”很高,圈外人也就是一笑了之。笔者愚昧,不知道书法艺术为何要“刻意”去和“西方文化”碰撞。不仅要碰撞,还要融合,还要接轨,还要走向世界。以致造成了,有的人以在西方办“个展”为幸,以洋人的称颂为荣。其实没有汉学底子的老外,看中国人的字,说得好听一点——也怕看不见中国“皇帝的新衣”,认为是“抽象艺术”,说得难听一点,如同是看巫师划的“咒符”——只不过人家不明说罢了。
和“西方文化”能够“碰撞”,自然不错。但不知和西方哪一家文化碰撞?且不说西方许多国家,地理、历史、民族、语言、文化情况各异,就是发达的“八国集团”,语言、文化也各不相同。如何去一一碰撞?就是最发达的美利坚——西方文化的“代表”,他自身的文化也是多元的,我们和哪一种去碰撞?和印地安?和黑人?和亚裔?还是和白人自己承认的必得主义、得意忘形、恃强凌弱、不可或缺的“世界警察”文化去碰撞?权威们可能会说,你这是抬杠,“连对手都没有找到就开始舞枪弄刀地瞎批判”——我们说的是碰撞西方的综合性的优秀文化。不错,笔者也认为是这样,也应该这样。但不知权威们说的西方优秀文化,优在何处?秀在何方?内容是什么?形式是什么?我方用什么去碰撞?用内容?用形式?还是都用?如果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还没弄明白,就去碰撞,只能是瞎撞。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当初恐怕也没有扬言和什么文化碰撞,然而如今却走向了世界,这并不是说英语——当地的傻子都可以说的话,有什么先进,而是借助了经济力和科技力。所以说“文化”尤其是书法要走向世界,还早着呢。当今,把碰撞做为一个目标,提出来,少数先行者去碰一下,撞一下,也可以。但千万不要形成“运动”,号召大家都去碰撞,好像不碰撞,中国书法就没了出路似的。具有5000年历史的汉语言文化——一种以象形文字为原材料的书法艺术,和西方以“拼音”为基础的文化相碰撞,其结果如何,权威们都说不清,走不通,咱们普通书者别去凑那个热闹。弄不好,成了“东施效颦”,不仅贻笑大方,还可能把自己的本份丢了。其实,用不着刻意去碰撞,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会通过各种方式和媒介接触一些“西方文化”,积累沉淀之后,就会自然地对书法创作产生作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比有意识地去碰撞,效果恐怕要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不能出国,又不懂外文(上千种的外文,没有人敢说都能弄懂)的普通书法爱好者,不要觉得不懂“西方文化”,就自惭形秽。因为说到底,书法是东方艺术,犹如油画是西方艺术一样,无论怎样碰撞,也改变不了它的本质和属性。让那些专门家们去碰撞吧,咱们普通书者还是老老实实地练字,说不定哪一笔就沾上了哪部美国枪战片的功夫——“枪”,也是美国的文化,咱们在电视上看的多了,自然就“融合”到笔下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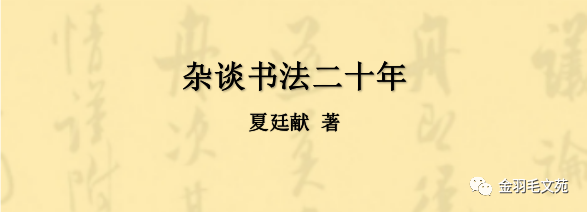
新“时代”,新气象。一个显著的“重要标志”是:口号多,流派多,而且几乎是一个口号一个流派,光是“主流派”,就号称“四大家族”。什么“现代派”——西方前卫,又拼又贴;什么“学院派”——主题先行,又制又作;什么“新古典主义”——民间书法,模仿新颖;什么“新文人书法”——尊重传统,崇尚学养;令我辈不入流没有派的普通书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写字”的学问也太大了!真不愧是“大文化”!笔者寡闻,但似乎记得历史上只有皇帝提倡、推行过什么书体,例如秦世皇搞过“书同文”。没有听说哪个大书法家写字时,对外宣布,我要创造一个传之千秋的流派。李斯是公认的“篆书”创造者,但他也只是跟着秦始皇到一些山头上立个碑,既没有提“秦始皇主义”的口号,也没有说自己是什么“皇宫派”或“山头派”“碑文派”。书圣王羲之以《兰亭序》扬名天下,也没听说他在生前搞过什么“兰亭派”组织,他的儿子王献之曾劝过他“大人宜改体”。可见“兰亭派”也没有形成——连他儿子都没“入会”。
“时代”到底不同了。当今的书家,不鸣则已,一鸣就有“口号”——提倡一个什么主义;有“流派”——成立一个什么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大旗一展,不愁没有跟随的人。否则,书展,选集,免谈。不管你赞不赞成他那个主义,愿不愿意入那个流派,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氛围,好像不喊某个口号,不入某个流派,就落伍了似的,就写不好字了似的。于是,只好随大流,想方设法按某个流派的风格“规范”自己,要么投向“西”,要么靠向“中”,要么趋向“不中不西”,以便登堂入室,走进书法艺术的殿堂,之于自己对书法的感悟,也就按下不提了。有人曾经说,书法界的风气相当浮躁。笔者妄言,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义”“流派”闹的。表面上看起来书坛相当热闹,实际上潜伏着一些危机。 口号终究是口号,代替不了作品。流派终究是流派,也代替不了作品。最终还是要“作品”说话,“后人”说话,“历史”说话,这才是最过硬的。历史上提过多少口号称过多少流派啊,有谁还记得着?传下来的只有作品!书法说到底是一种“个体劳动”,口号——主义也好,流派——群体也好,可能会对书法创作产生一些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个人的体验和觉悟。因此,普通书者且莫妄自菲薄,“主意”自己拿,流派合意者参加一下也无妨,不参加也无所谓——拜碑帖为师也完全可以。切莫被“口号”“流派”吓得无所措手脚,摸不到门户。不就是写字嘛,平心静气地练就是了,只要功夫深,不愁铁杵磨不成针。即如磨不成针又咋的,还能去跳河?吴冠中那样的大家还说:笔墨等于零。把笔墨的事都看透了,还说咱这些小人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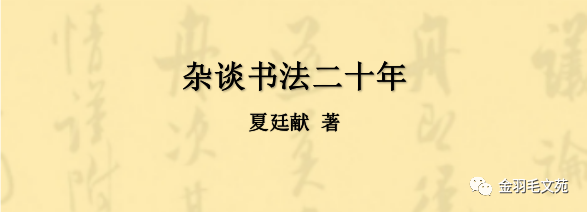
有人戏言,往人群中随便扔块砖头,就能砸住三个书法家,可见书法家之多。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在众多的书法家中,不乏“含金量”高的。但无庸讳言,也确实有南郭先生。前几年,某省明码标价,30万元,给个书协主席当。副主席、理事,均有标价。后来虽说没有搞成,但已经说明,这些书法家另一种意义上的“含金量”。的确,这年头,你只要有钱,办个“个展”,出个“作品选集”,一点都没有困难。有的书法家名气很大,除了书外功夫“高”——傍“款”傍“官”(大贪胡长清身边就有好几位书法家围着转),还有书内功夫“巧”——巧“取”豪“夺”。一位“著名”的——起码排在全国前30名内的书法大家,不少名山大川都留下过墨迹——字也是写得不错的。为了显得自己不仅能写,还有书法“理论”,1997年,竟把一个无名小卒呕心沥血撰写的书法文章的精华“取去”,成了自己的“大作”,连题目都没改——因为题目是一家之言,太好了!他大约不忍心改。小卒怎么能和“大家”较量?说到哪,也不会有人信。于是,小卒只好忍下了这口“鸟气”。由此可见,有的书法家的“著名”,是“诛”了别人的名。
字练到一定程度上,就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阶段。同一个人的字,有的人看了,觉得好得很;有的人看了,觉得差得很。书法史上,这种例子多得很。远的不说,就说近代康有为的字,有人认为是“神品”,有人则怒斥是一堆烂草绳,无势无力无气。你看,就有这么大的差距!所以,要把这事看开了,不要被一些书法家的名气唬住了,觉得他那个字就好,自己的字就一钱不值,他的话(著作)就一句顶咱一万句,没那么回事。他们是人不是神,也会说错话,办错事,写错字——甚至写错常用的字。有的著名书法家的眼光也不比普通书者高到哪里去,只不过他的“位置”高罢了。好像到了那个位置上,水平就有了,没那么回事。练自己的字,养自己的心,管他什么家的“名气”。你把他看透了,他也就在你面前不好再招摇了。你把书坛看透了——500年后留不了几个“家”,也就对熙熙嚷嚷的书坛一些怪现象理解了。还有一些“不要”,例如,不要被“书法展”迷惑了,收参展费的书法展最好别参加。当然,你要参加也可以,那就得有“献金”的思想准备。再如,不要被一些大部头的书法理论著作迷惑了,那些宏篇巨制,多是抄来抄去,错讹不少,新意不多。重复,矛盾,含糊,互贬,胡诌,自尊,令人难以卒读。别花那个冤枉钱——定价都很高的,别耽误你的功夫。还有……不说了,再说就眈误对话者的功夫了,打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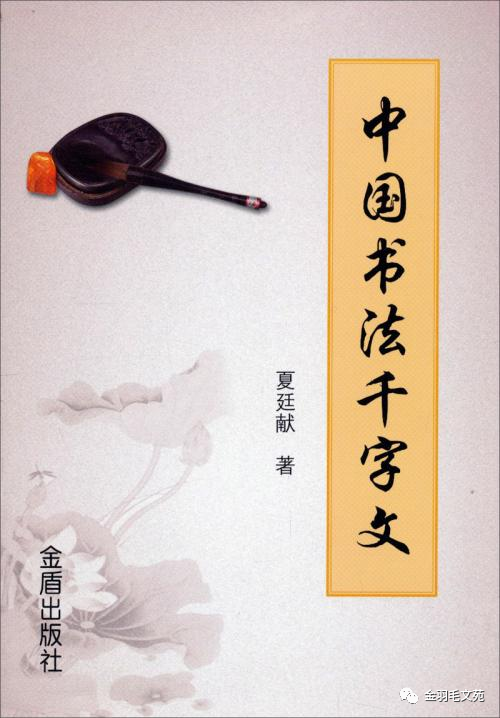
《中国书法千字文》金盾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夏廷献,河南省南阳市人。1944年出生于农家, 1964年入伍,1999年从海军装备部某局政委岗位退休(海军大校)。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幼时写大仿,与书法结缘。中学时,受到书法家王学睿老师直接影响,对汉隶魏碑产生兴趣。参军后为连队书画骨干。1970年后在各级机关主要从事“文字”工作,业余时间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汉字的“生命形态”。1999年出版了专著《书道犹兵——中国书法艺术新探》,提出了“战争是书法艺术之父”的观点,揭示了“兵法与书法”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关系,探索了二者同理、同法、同势、同美的内在规律。行家认为是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为孙子兵法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为书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出版《中国书法千字文》(《金盾出版社》2014年1月)。1999年之后在《书法导报》等专业报刊发表书法评论文章三十余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戏剧脚本、游记文学、工具书等。

欢迎关注本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