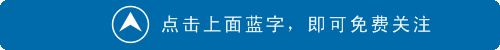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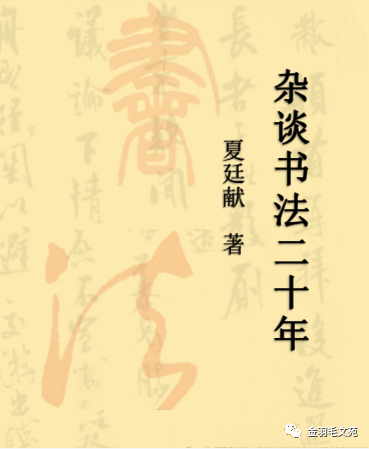
这是作者从1999年到2019年发表的书法评论文章汇编;是一部从普通读者角度辩证论述书法知识的“通俗读本”。全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涉猎到书法的基本理论、毛笔形成、基本笔法、骨文来历、汉字特征、结字技巧、草书格局、章法营造、法帖分析、书法鉴赏、书法命运、先贤经验、自身体会等。提出了诸如“超长画”“超大字”“神布局”“使用‘黑体’”“接纳‘饰书’”“书法精神”“书作‘三品级’”等新概念和新观点;记录了向当代22位书法家请教学习、采访交流的情况。是作者20年间对中国书法艺术观察与思考的“文字足迹”。 翻阅书法理论典籍,常常看到“······不是书”或类似的警句,仔细琢磨,感到从这些“不是”中,颇能领悟到“是”的启迪,今特辑录如下: 书法家李斯强调用笔之法,要“信之自然,不得重改”。就是说,落笔成形,点画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能再重描重改,因为重描重改的点画必不“自然”,而“自然”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准则。李斯此语,不仅划清了“书法”和“写字”的界限——写字尤其是写美术字是可以重描重改的;也划清了“书法”和“图画”的界限——图画是可以重描重改的。唐代书法家蔡希综在《法书论》中也说过:“其有误发,不可再摩,恐失去笔势。”强调了书法是“一次性”挥写成功的艺术,即如笔画有失误,也不能再去描摩修改,否则,就失去了笔势。“重改”不仅是初学者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也是当今书坛一些书者“明知故犯”的一个问题。重申“重改”不是书,把那些制造拼贴的所谓什么派的作品划出“书法”的范围,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法言》中说:“断木为棋,浣革为鞠,亦有法焉,而况书乎!”浣革,刮磨皮革。鞠,皮革制成的皮球。扬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锯断木棒制作棋子,刮磨皮革制作皮球,也都有正确的方法,何况学习书法这样比做棋子、皮球还要难得多的事,怎么能不依“法”——规律、规矩办事呢?换句话说,不依“法”写字,就不是书。把“书”和“法”联系起来,扬雄恐怕是第一人。因此,扬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后来“书法”一词的最早出处之一。也就是说,在两千多年之前,先贤已经认识到了书是要有“法”的。 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在《笔论》中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蔡老先生认为,书法的起源来自“自然界”,因此作书时,就要将人和自然界的某种形态“化入”书体之中。“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矛,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每一个字,甚至每一笔画都应该成为有生命的“个体”。“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整个字纵横交错的线条和字体造型,都同人的某种动作或自然界的某种形象有相似之处,才可以称之为书法,否则就不是。蔡邕的说法,在文字还没有完全脱离“象形”阶段是可以做到的,在文字的造型越来越远离自然形态、越来越“抽象”的情况下,要做到字字“入形”,是很难的。但作为书法的一种最高境界追求,还是有必要的。所以东晋的女书法家卫铄也强调说:“每为一字,各象其形。” 书圣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说:“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点画耳。”“算子”,古代计算用的筹子,形状如同小木棒,长6寸左右。王书圣这句话的意思是:若是横画竖画写得像算子一样平直相似,没有差别,字的上下左右都平平正正,十分呆板,就不能说是书法,只能算是写出了字的点画,毫无艺术价值。这句话,可以进一步导出:直来直去的单调用笔不是书——非“一波三折”不可;周边“外围线”整齐呆板的字形不是书——非“参差不齐”不可。所谓“参差不齐”,就是要时偃、时仰、时欹、时侧、时斜、时小、时大、时长、时短,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笔势。这就好比:人站在高台上跳水,直着跳下去不是艺术,翻几个跟头打几个转儿下去——有了曲线才是艺术;这句话中的“状如算子”比喻,由于形象生动,常被书家引作书评用语。 晋代书法家虞安吉曾经说过:“夫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象本,乃转自取拙,岂是书邪?”这里说的“书意”,指书法的意境、意趣。本,指范本——临摩的碑贴。邪,疑问语气。虞安吉的意思是说,临摹古人的法书,不理解字的意趣,只在一点一画上追求外形与范本相似这乃是自取拙劣,哪里称得上是书法呢?虞安吉是较早提出“书意”概念并强调临帖要理解“书意”的书法家,“书意”概念的提出,不仅为后来的“神似说”开了先河,还为如何临帖指明了方向,划清了“非书”与“是书”的界限。唐太宗李世民十分赞成虞安吉的观点,不仅在《指意》一书中引用了虞的话,还进一步发挥说:“纵放类本,体样夺真,可图其字形,未可称解笔意。”由此可见,理解古人法帖神采、意境的重要。 唐代书学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孙氏这句话是批评有些人随意用笔写字,胡乱抹成字形;心里不明白临摹的正确方法,手下也不懂得挥毫运笔的道理。这样写出的字还想美观好看,岂不是荒谬之极!意思是说,要想学习书法,必须从临摹开始,在点画用笔是下苦功夫,决不能任笔为体,草率成字——那样写出的字不是书法,只能叫“涂抹”。想到当今书坛一些用笔涂抹甚至连笔也不用的涂抹,孙氏“任笔为体”不是书的思想,仍具有现实意义。 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 灌在《评书药石论》中说:“为将之明,不必按图讲法。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无方皆能,遇事从宜决之于度内者也。”意思是:将领的英明之处,不是看他打开阵图讲兵法,而是要看他能否根据战场上的敌我形势,决定战略战术,克敌致胜。同样道理,书法创作也不必完全按照书本上规定的规则去做,而要专在“应变”上下功夫,用笔、结字、布局都要按照自己心意的支配,审时度势随机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好字,才算进入到了书法的妙境。墨守现成文本之规,不敢越固定法则一步,那样写字,便不是书。张氏的这一论述,窃以为主要是对有书法基本功的书者讲的,初学者不可随便套用,以免“欲速则不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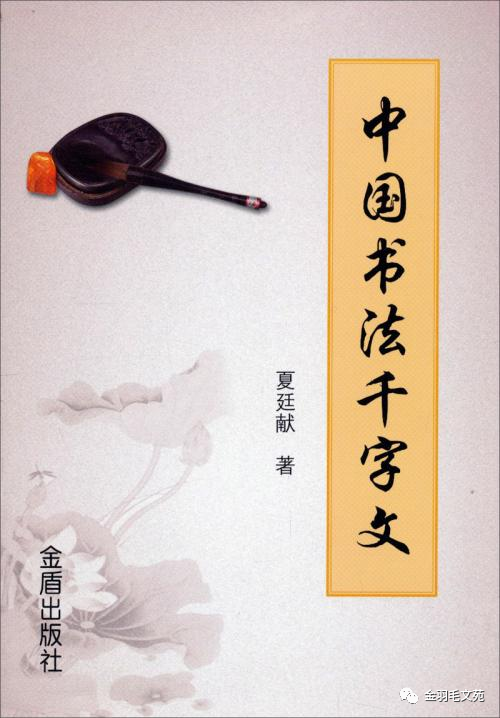

夏廷献,河南省南阳市人。1944年出生于农家, 1964年入伍,1999年从海军装备部某局政委岗位退休(海军大校)。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幼时写大仿,与书法结缘。中学时,受到书法家王学睿老师直接影响,对汉隶魏碑产生兴趣。参军后为连队书画骨干。1970年后在各级机关主要从事“文字”工作,业余时间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汉字的“生命形态”。1999年出版了专著《书道犹兵——中国书法艺术新探》,提出了“战争是书法艺术之父”的观点,揭示了“兵法与书法”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关系,探索了二者同理、同法、同势、同美的内在规律。行家认为是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为孙子兵法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为书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1999年之后,出版了《中国书法千字文》。在《书法导报》等专业报刊发表书法评论文章三十余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戏剧脚本、游记文学、工具书等。

欢迎关注本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