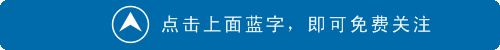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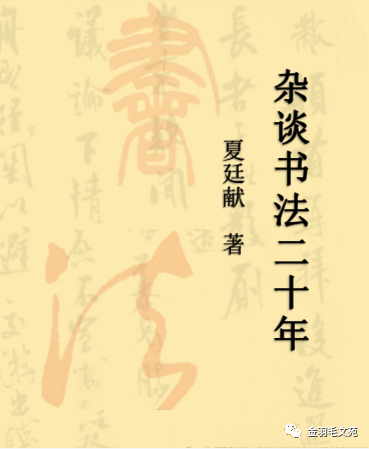
这是作者从1999年到2019年发表的书法评论文章汇编;是一部从普通读者角度辩证论述书法知识的“通俗读本”。全书观点鲜明,内容丰富,涉猎到书法的基本理论、毛笔形成、基本笔法、骨文来历、汉字特征、结字技巧、草书格局、章法营造、法帖分析、书法鉴赏、书法命运、先贤经验、自身体会等。提出了诸如“超长画”“超大字”“神布局”“使用‘黑体’”“接纳‘饰书’”“书法精神”“书作‘三品级’”等新概念和新观点;记录了向当代22位书法家请教学习、采访交流的情况。是作者20年间对中国书法艺术观察与思考的“文字足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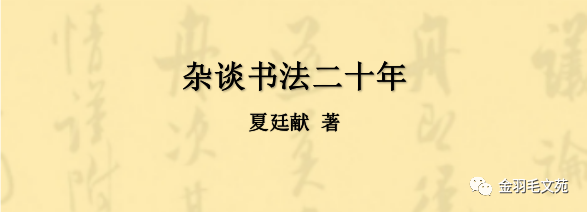
——“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源头、母体和通脉”读后杂感 拜读《书法导报》2012年2月8日第10版刊登的李正宇先生大作《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源头、母体和通脉》之后,觉得该文有以下三个“之嫌”:1、有 “自设靶标”之嫌。李先生开句说“以往各种版本的《中国书法史》,基本上只是‘汉字毛笔书法史’…… 这种荒谬的观念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书唯毛笔’。”先生这种说法,有点“一篙打翻一船人”。实际情况并不是“以往各种版本”都只讲“汉字毛笔书法史”,也不是先生说的“后世多不知古用硬笔写字的实况”。笔者撰写的《刻刀论纲》(郑州《寻根》杂志1998年06期)就阐述了“刀笔”——硬笔在创造保存汉字、形成书法艺术(用笔、结字、章法)中的重大作用。李先生把一种说法概括为“荒谬的观念”后,自己“归结为四个字:‘书唯毛笔’。”——自我设置一个“靶标”,然后便开始“放箭”——全文基本上是向这个“自设靶标”不断发起“攻击”。尽管一些说法不无道理,但由于“自设靶标”在前,很大程度上减弱了说服力。从阅读心理学上说,也容易引起读者“反感”。2、有“对空放炮”之嫌。既然事实上并不完全存在李先生设定的“靶标”,那么,先生引经据典用五六百字论述“‘书唯毛笔’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岂不就是“对空放炮”?文中还说到“……发现新石器时代彩陶,考古家又臆断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也是用毛笔绘制而成。于是将使用毛笔的历史更提前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将‘书唯毛笔’观念发展到‘书、画唯毛笔’,大大强化了这一错误观念。”笔者认为考古家们“将使用毛笔的历史更提前到新石器时代”,一点没有错,甚至还晚了。因为最普通最浅显的道理是:有字时即是有笔时——字是笔划拉出来的嘛。至于是什么笔?可以再讨论。文中认为考古家们“进一步将‘书唯毛笔’观念发展到‘书、画唯毛笔’,大大强化了这一错误观念。”笔者认为考古家们并没有这么做,是先生又自设了一个 “书、画唯毛笔” 的“靶标”。这种将“无辜者”推向“审判台”的行文方法,更是“对空放炮”。作为学术文章,似乎不那么严谨。3、有“意气用事”之嫌。文中说“但‘书唯毛笔’的错误观念已经流行两千余年,偏见经久,凝为偏执,而余说面世未久,传之不广,愿借此机会,再作申说。”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由于主观、偏激产生的任性情绪,感情也显得冲动。基于不是“平心静气”的探讨问题,先生在5000多字的“申论”中,难免就有点“偏执”的武断。这里摘其要与先生商榷。其一,文中说“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的刻、画工具是硬笔,不是毛笔”。笔者认为这么说,有点太绝对。拙见是,中国书写工具——笔,和文字(符号)一起甚至早于字符诞生,它的发展历程是:硬笔(骨、棒、箭头、刀具等)——类毛笔(毛笔雏形——在棍棒上扎上兽毛的“兽毛捆扎物”)——准毛笔(具有扁刀形、圆锥形两种主要形状的“兽毛捆扎物”)——毛笔(具有尖、圆、齐、健四德的成熟文器)。因此,“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的刻、画工具”不绝对“是硬笔”,“准毛笔”也参与了刻画。先生举例的图5“大地湾出土彩绘符号”,图7“双耳瓮·甘肃永登出土”, 应是“扁刀形准毛笔”运动中变换角度刷成(因是准毛笔,所以没有“四德毛笔”运动时“必然出现的提捺、抖颤之迹”)。若是纯硬笔,难以勾画出图7那种十分流畅却又粗细不一的圆形线条。其二,文中说“甲骨文、大小篆、古隶、秦隶尽属硬笔书体”。笔者赞成先生在文中把古字分为“本体字”“加工体”——“美术体”的看法。拙作《书道犹兵——中国书法艺术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发行)也阐述了金文、石文是古代“美术字”的观点。但不大赞成先生把“秦隶”完全划入“硬笔书体”。拙见是,“秦隶”可以是“硬笔书体”,但也可以是软笔——毛笔书体,因为秦时,较为成熟的毛笔已经诞生(传闻由大将蒙恬改良成功),从篆书——删繁就简到隶书,是毛笔运动的产物。史载是秦始皇时期因善书供职王室的下杜(今陕西安南)人程邈创造的。其三,文中说“硬笔书法是我国书法的源头、母体和通脉”。笔者觉得这种说法有点笼统,值得推敲。拙见是,古代硬笔书法是现代硬笔书法的源头、母体和通脉(现代硬笔书法不是“舶来品”),为软笔——毛笔书法艺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规范基础。但毛笔的辉煌——在创造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四大书体、各种流派无数种风格作品,造就历代书法大师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硬笔难以做到的。总起来说,硬笔书法和毛笔书法,都为中国书法艺术乃至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没有硬笔,汉字难以创造出来,没有硬笔(箭头、刀具),汉字难以在甲骨上保存下来——书法也就没有了“原材料”。同样,没有“四德毛笔”“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蔡邕《九势》)的复杂运动,也难以形成“一字千面”、“一字见人”、“心正笔正”的中国书法艺术。笔者虽然孤陋寡闻,但作为书法爱好者,多年来看过不少书法著作,并没有看到和接受先生所说的“代代相承,往而不返”“‘书唯毛笔’的荒谬观念”,也没有“陷入‘书画唯毛笔’的泥潭”。先生论述硬笔书法的历史作用无可厚非,很有必要,也有道理。但把书写“汉字毛笔书法史”看做是“荒谬”“错误”的事,义愤填膺地大加鞭挞,有点过了。因为在学术上,一直有人认为成熟的“四德毛笔”诞生之前,古人是“写字”,不是“书法”。写字和书法是两个概念,中国书法史应该从有毛笔开始写。笔者认为,写字和书法,确实是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写字,准确可识即可,书法则要按艺术规律办事。搞书法首先得会写字,不会写字不可能从事书法。但不争的事实是,人人都可以学写字,但不是人人都能成为书法家,真正成为书法家的只是极少数人。基本事实是,有史记载的历代书法大家都是使用毛笔的。从这一点上说,把“四德毛笔”诞生之前的古人用硬笔“写字”,不放在“中国书法史”中,也有一定道理。如果不赞成这样做,可以讨论,但“火气”不要太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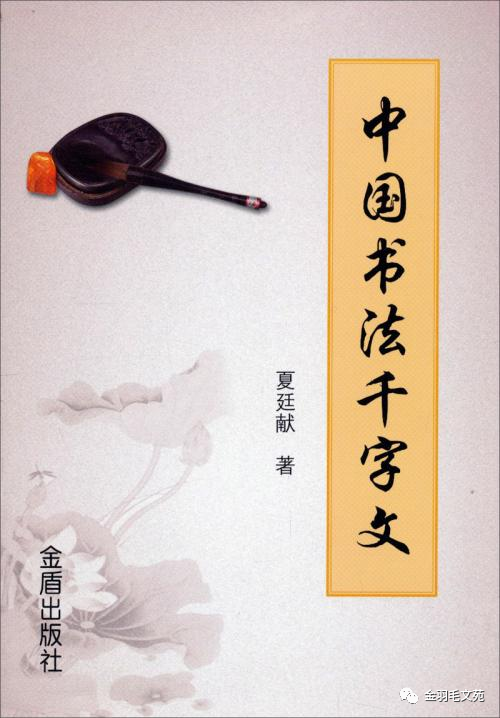

夏廷献,河南省南阳市人。1944年出生于农家, 1964年入伍,1999年从海军装备部某局政委岗位退休(海军大校)。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幼时写大仿,与书法结缘。中学时,受到书法家王学睿老师直接影响,对汉隶魏碑产生兴趣。参军后为连队书画骨干。1970年后在各级机关主要从事“文字”工作,业余时间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汉字的“生命形态”。1999年出版了专著《书道犹兵——中国书法艺术新探》,提出了“战争是书法艺术之父”的观点,揭示了“兵法与书法”的历史渊源及其相互关系,探索了二者同理、同法、同势、同美的内在规律。行家认为是独树一帜的一家之言,为孙子兵法研究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为书法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1999年之后,出版了《中国书法千字文》。在《书法导报》等专业报刊发表书法评论文章三十余万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戏剧脚本、游记文学、工具书等。


欢迎关注本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