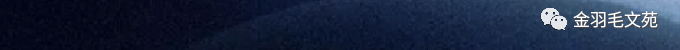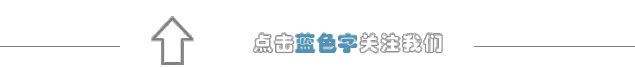

编者:著名军旅作家陈明福曾出版过《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左宗棠传略》和《湖南出了个左宗棠》等纪实文学作品,他写了《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32篇证据确凿、信息量大,文笔生动、可读性强的系列文章。本文转载于东岳客(ID:rmrbssd),以飨读者。
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
(三十一)

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时任两江总督、为尽职到处奔波的左宗棠,旧疾增剧,他上疏自陈病情,皇上温旨慰留,予假三月养疾。当时,皇上和朝廷确实也有“苦衷”,这就是强敌法军入侵,国难当头,无人能挺身而出,只有在他这个老迈之人、老病之身上打主意,恰如杜甫在《古柏行》诗中所咏叹之句:“大厦如倾要梁栋”啊!那些随风摇头晃脑的“离离山上苗”,怎堪当此重任!三个月后,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他亲自到吴淞口和沿江查阅防务,恰逢彭玉麟由湖北查案回船到江阴,两人约好在吴淞口相会。彭玉麟和左宗棠是湘军中老同事,二人都是主战派,意气相投。彭玉麟看到他增购船炮、加强海防的各项布置,十分高兴,说:“布置如此周密,不怕外国人来,只怕他不敢来。”九月十三日,左宗棠动身离宁,取道江西去福建履任。福州官绅士民听到他即将到来,都欢欣鼓舞。他于十月中旬进入福建,二十四日由延平起程,福州司、道、州、县以及文武官员陆续前往离福州约一二百里的闽江岸的水口和竹崎迎接。左宗棠的行辕大厅中挂了一幅欢迎的对联:十月二十七日左宗棠抵达福州,全城官员聚集在洪山桥接官亭迎接,士绅和老百姓则在浙绍会馆迎候。据《申报》记载,当时盛况空前,一路所过之处,街坊店铺,都摆设香案,放炮燃香;全城人士扶老携幼,争先快睹者,以数万计。甚至幽闺琼姬,小家碧玉,如云如水,都以一望丰采为荣。左宗棠于下午2时入城,见到他的人都说他精神矍铄,不减从前。有一位署名“采樵山人”的目击者,在《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一书中记载说:钦差大臣左宗棠进入福州时,威风凛凛,旗帜飘扬,上面大书“恪靖侯左”字样。队伍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后面一人乘肥马,执长鞭,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主将左宫保是也。自马江战败后,福州官民一夕数惊,风声鹤唳,在此时:想帷幄运筹,訏谟独裕,蠢尔法人,当不难灭此朝食也。到福州的第二天,廿八日黎明,左宗棠即去拜会总督、将军、巡抚,布置地方防务,听取他们的汇报。廿九日,拜谒林文忠公则徐祠。这位昔日抗英的英雄,逝去倏忽已三十年了;回忆当年湘江舟中夜话,宛如昨日。林则徐谆谆叮嘱:“中国之大敌,其俄罗斯乎!”如今新疆已收复,俄罗斯的凶焰暂时收敛,法兰西又来了。中国人如不自强,敌人将会一个接着一个来,有时还会联合起来侵略中国,左宗棠在林文忠公祠前悼念徘徊,不胜感叹。到福州后首要任务,是加强海岸防守。兵船虽已丧决殆尽,还有炮台要塞。闽江入口北岸的长门和郎琦岛上的金牌是两处要隘,左宗棠命迅速将该两处炮台修复,又在闽江口竖立铁桩,用铁索拦江连结,没入水中,用机器操纵,只准许本国船只通过,如敌船来,就将铁索升起,使其无法进入。又在距省城30里的林浦、魁歧及闽安右路出海的梅花江,都用垒石填塞大部分江面,仅容小船通过。以上各处都建设炮台,派兵驻守。又命将海口水道标志立即取掉,船港遍布水雷,将沉没于马江的兵舰上的舰炮,千方百计卸下来,移装到陆上炮台。经过这一番布置,沿江沿海防务较前大为巩固。抗法斗争的另一条战线谅山、镇南关一带,法国以主力部队攻击王德榜驻守的丰谷。王德榜军奋勇抵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伤亡惨重,军火已不继,援军苏元春部违命不到,王德榜只得率军突围,退到车里。法军就转而进攻潘鼎新驻守的谅山。潘鼎新急命王德榜军来援。王德榜的部队还没有赶到,潘鼎新的守军在法军猛烈攻击下,毫无斗志,不战而溃,谅山、镇南关失守,完全是潘鼎新秉承李鸿章投降路线的恶果。但他后来把责任推在主战派、英勇抵抗的王德榜身上,将自己接战便溃百般掩盖。当潘鼎新军队狂奔乱窜时,王德榜和老将冯子材约定,二人率部坚守阵地,伺机打击法军,由冯子材守凭祥,王德榜守由隘。
法军在攻占镇南关后,法军统帅尼格里派人在废墟上插块牌子,狂妄地写道:但他们又发觉自己是孤军深入,不敢久停,就放火烧关,军队退到文渊。冯子材于是趁机率军进入镇南关内,与驻守由隘的王德榜部互相呼应。鉴于镇南关已被焚毁,冯子材选定距关十里的关前隘构筑防务,在隘口垒起一道长墙,挖掘长壕,以备攻守。同时,他又积极团结边境其他部队,激励他们协同作战;还同关外的中越群众取得联系,帮助他们武装起来,乘虚捣敌军后路,截杀逃敌。与此同时将法国人的牌子拔掉,另换一块,上面写道:二月初七日,法军不甘心失败,再度来犯,几次猛袭关前隘,冯子材军一连失去数垒,形势危急。王德榜及时从由隘派兵来援。法军没存料到这一支奇兵,毫无防备,后路部队被全部歼灭,军火辎重也都被王德榜军缴获。1885年3月23日,法侵略军倾巢来犯,在关前隘激战终日。次晨,侵略者乘雾鼓噪扑来,炮声震谷,枪弹雨集,长墙有几处已被轰塌,一些法国兵由指挥官持枪吆喝着,企图爬墙冲入。随着一阵连珠炮响,栅门大开,冯子材挥动长矛,一跃而出。兵勇们就潮水似地涌出栅门,奋勇争先,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压向敌人阵地,刀劈枪挑。侵略军惊呆了,霎时旗靡阵乱,炮声顿哑。突然,阵后又杀声大起,关外中越群众一千多人风驰电掣地冲杀进来。侵略军全线崩溃,一个个丢盔弃甲,拔腿就跑,翻岭越涧,仓皇逃命。各军乘胜追杀十多里,毙敌官兵一千多人。法军统帅尼格里受重伤,躺在担架上星夜南窜,这时,他恍惚理解一些,中国人在镇南关上写的那句重建门户的话,意味着什么。冯子材、王德榜两军将镇南关营垒全部收复,苏元春军也加入作战,三军联合进攻敌军,当夜收复谅山,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镇南关——谅山大捷”。清军一直追赶法军到坚老。同时,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西线也获得临洮大捷。
当法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引起了法国全国上下的震动。发动侵略战争的茹费里内阁在法国人民的抗议和反对派的攻击下随之倒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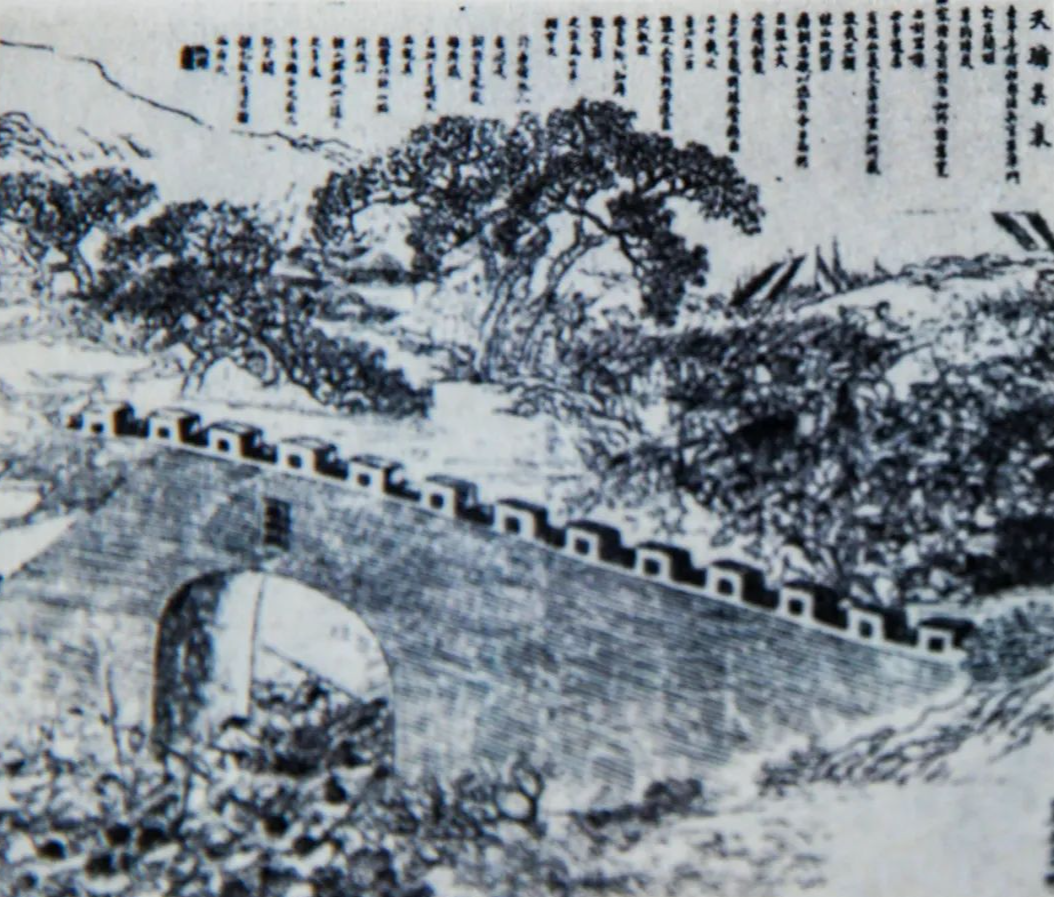
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1885年6月4日),李鸿章和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给予法国在广西、云南通商的特权,包括减税等利益,规定以后中国在这两省修筑铁路时,要与法国协商会办。由于法军在战场上战败,没有索取“赔款”,并答应从基隆和澎湖撤兵,投降派认为面子上已过得去,条约立即得到清廷和慈禧的批准。这项条约不仅不敢抗议而且公然承认法国占领越南、开中国西南大门,使法国人得以长驱直入。这项屈辱的条约是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之后签订的,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闻!中法和约的签订,是对左宗棠的一个重大打击。他闻讯后悲愤无比,但回天乏术,徒呼奈何!他以古稀之年,多病之身,来到抗法前线,全凭着一股爱国热忱,而今战事已经结束了,屈辱的条约已签订了。投降派不但不以为耻,反而气焰嚣张。他的两员抗法部将都遭到不白之冤,种种事实无不使他痛心疾首。当时他的病势已很严重,他曾描述自己的健康情况:“自到福建以来、食少事烦,赢瘦不堪;手臃颤摇,难以握笔,批阅文件,万分吃力;时间稍长,即感心神徬徨无主,头晕眼花。有时浑身痛痒,并经常咯血;偶尔行动,即气喘腰痛。”六月初十夜间,忽然痰涌上来,气喘不已,手足抽搐,昏迷过去。医生赶紧进药急救,经过十个多小时,才苏醒过来。他自知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思前想后,国家仍如此积弱,许多曾想要办的事都没有来得及办,于是竭尽最后一点衰微的精力,将所考虑到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一连上了两道奏折,第一道是:《复陈海防应办事宜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第二道是《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驻台镇摄折》。1885年9月5日,台风袭击福州,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左宗棠处于弥留时刻,满怀悲愤和遗憾之情,口授遗折,由其子孝宽在榻前笔录,缮交福州将军穆图善、陕甘总督杨昌浚,转奏于清廷。后来《皇朝经世文三编》编者陈忠倚,在将这篇遗折辑入该书时特作跋说:“此疏……虽恳恳数语,恰中我中国之病源。阙后文酣武嬉,边防不整,中日之役,果不出公所料。公真神人矣哉!”
他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突然他醒过来,这是回光返照,眼睛似乎出现一道光明,恍惚回到柳庄门前,正和周夫人、全家为灾民施粥施药,眼望着灾民一群群走过去,心头充满着同情和叹息;忽然又回到了那间梧桐塘书屋,白发苍苍的祖父在教他咿咿唔唔念书;忽然他又到了空旷寂寥、风沙弥漫的西征路上,远望着白雪皑皑的天山山脉,回忆湘江夜晤时林公的谆谆嘱托……然而,一霎那一切都过去了,眼前又是一片昏暗,病榻前儿子和亲人们见他低声喃喃自语:“哦哦!出队!出队!我还要打。这个天下,他们久不要,我从南边打到北边,从西边打到东边,我要打……”(参见《汪康年笔记》卷8)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终于那双目光炯炯的眼睛阖上了,他停止了呼吸,告别了曾经生活、战斗73个年头的人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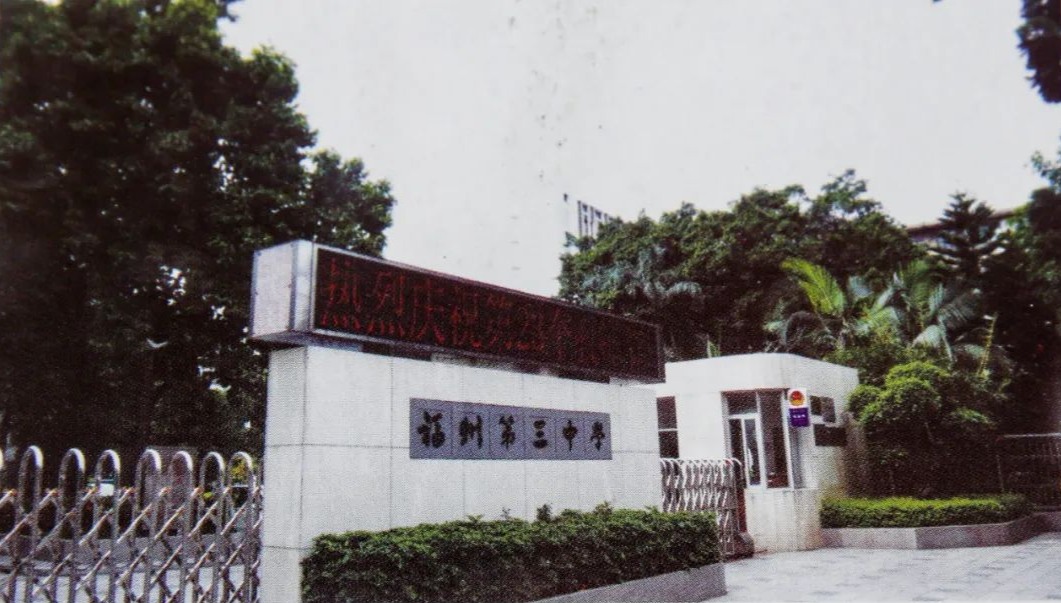
福州城经历了一整天的狂风暴雨,那天晚上,城东北角崩裂2丈多宽,城下居民却未受到损害。大雨下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左宗棠逝世的噩耗传出,一位署名“采樵山人”的福建士人记录了当时的情形说:福州“城中巷哭失声”“全城百姓,闻宫保噩耗,无不扼腕深嗟,皆谓朝廷失一良将,吾闽失一长城”;军队中,“一时营斋营奠,倍深哀痛”,“归丧之日,江、浙、关、陇士民闻之,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 
陈明福,1937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原海军大连政治学院专业技术四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辽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大连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登临西岳华山
已出版专著、作品36部,逾1200万字,还有多部待出。已出版的有《“重庆”舰举义纪实》《海疆英魂》等四部中华名舰系列,《杞忧集》等三本杂文,《朱可夫兵法》等两部军事谋略论著,《古今海战》等七本海洋科普读物,《古今海战》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沧桑旅顺口》等五部纪实文学,《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苏东坡大传》等六部人物传记。2013年6月,《晚清名将左宗棠全传》获五年一评的第四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颁奖词曰:“古稀之年的陈明福,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充沛的激情,历时六载,寻着晚清名将、中兴名臣左宗棠的足迹遍访关内塞外、天山南北、万里海疆,查阅搜集了数千万字的史料和不少趣闻轶事。作品气势恢弘,文笔流畅,叙事生动,成功塑造了左宗棠鲜明的人物性格,展现了这位民族英雄传奇的人生历程,填补了百余年来在左宗棠传记写作中的缺憾和不足,并对有关左宗棠的种种争议,亦力求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2012年被评选为大连市文艺界“十位有影响的人物”。2018年8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徐锦庚著的40万字长篇报告文学《大器晚成》,《人民日报》9月7日副刊发表《以沉雄之笔写峥嵘岁月》1700字的评论文章,《浙江日报》也发了张宏图的评论。《现代金报》发表张登贵《一部书,两个人》的评述,《宁波日报》《衢州日报》等转载。结语是:中国,太需要这样有品格的知识分子了!
前文回顾
“中国近代海军开拓者”|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
三顾沈门|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
羽书皇命急催西行|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3)
兵饷粮运艰难万状|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4)
缓进急战|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5)
出关祭旗|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6)
一炮破三城|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7)
衔枚疾走|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8)
摧毁阿古柏政权|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9)
粉碎阴谋|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0)
丧失伊犁|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1)
“天下之事作吾事”|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2)
锋指伊犁|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3)
舆榇出关|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4)
肃州佳话|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5)
途中多险|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6)
十年交涉|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7)
功在千秋|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8)
清正廉洁|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19)
清苦澹泊|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0)
务本为怀|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1
卖字充饷|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2)
利国惠民|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3)
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4)
玉门出塞|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5)
安抚回民|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6)
严劾成禄|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7)
跺脚骂殿|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8)
锋颖凛凛|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29)
援台斗争|左宗棠在西北的那些事儿(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