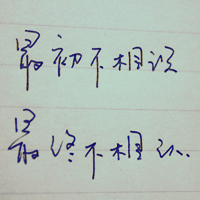操练歌声
以下文章来源于窥海楼 ,作者刘俊科
专注情怀,潜心原创


广播里几乎天天都在播送那首著名的长诗——《西沙之战》,衬托这首诗的音乐,可以说是军歌的集合。我就踩着这首诗的韵脚当兵入伍,穿上了水兵服。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我们用脚步去丈量;爱有多深,情有多长,河水在阳光下闪闪亮”。这歌就是写给我们这群当兵的人的。我们要去丈量山川江河,去丈量边陲海防。只是欢送我们的电影是《决裂》,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意义的影片,跟我们的“丈量”无关。但那晚在县大礼堂里放映之前,一个带兵的干部说让新兵们唱支歌,一个老兵在前面大喊:“都看我的指挥!”然后就“向前向前向前……预备唱”,我们是些没有训练过的新兵,还不会走齐步,哪能唱到一块去。好在那时候这些歌词都记得,也就都扯着嗓子喊起来。再看那个指挥,就像《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那个指挥,笨拙得很呐。我当时就有些跃跃欲试,只是忍住了。可能是我唱得起劲,还是因为我唱得稍微好听,一唱完歌,我的肩膀就被人拍了一下,一回头,是带兵的干部,他居然给了我两粒仁丹——那是那个时候的润喉佳品了!
那两粒仁丹哇,让我一想起来,咽喉里就有丝丝的凉爽!

其实,我对音乐的理解和应用,仅限于“简谱”的水平,玩过的乐器也不过是“大正琴”、“口琴”和“二胡”之类,且都是业余中稍次的那个水平。后来我觉得我对于音乐,理解高于应用,说得比唱得好听。那是著名指挥家卞祖善来我们部队讲座《艺术与人生》,讲毕,首长让我代表性地讲几句,我就讲了一小段关于军人与军歌、音乐与人生之类的话,没想到大师却紧握我的手说:“想不到军人对音乐能理解得这样深。”
我想,军人对于音乐的理解,更多的还是与战争、与和平相联系,不完全是艺术层面上的理解,而是超越艺术后,把将士的血和泪,胜利与荣光化成歌声来抒发胸臆。

新兵们来到部队,在学习齐步走和整理内务的同时,便开始学唱歌,蹒跚着走路,也咿呀着操练起歌声。
我到部队学的第一支歌是《潜艇兵之歌》。因我们是潜艇兵,这歌是必须学的。区队长将这支歌抄在黑板上后,我就有些显摆地小声哼哼起来,这一哼被区队长当人才了。从此就成了教歌员,也是“指挥员”了。每逢集会、看电影各学员队就是一场唱歌比赛,各队指挥也就到了骄傲自豪的时候。这次你输了,下次你就想赢回来。拉歌词更是五花八门,各有高招。
“××队,来一个,来一个,××队!”这是最初级的。
“××队不唱行不行,不——行,算了吧?不——行!”这就有点意思了。
“叫你唱,你就唱,扭扭扭捏捏不像样,不像样!”伴以有节奏的掌声,这就有内涵了。
也有编成山东柳琴的,也有编成河北梆子的,礼堂里那真是歌的海洋,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开会或开演的铃声不响,那歌声是停不下来的,真是激情四射!

当然,教歌也是有讲究的。大都要追求个出其不意。我教我的学员们唱《地道战》。“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整个礼堂都为我们鼓掌,你说那还不是胜利吗?《少林寺》电影刚开映不久,我们就会唱“少林少林,有多少故事把你传扬”,那全团的掌声又一次送给我们,学员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那些天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家学习工作那个起劲呀。不过,大家伙的嗓子都疼了。我们炊事班给大家煮了胖大海润喉。这让我想起了那两粒仁丹,便心生慨叹:当年的跃跃欲试,居然成了纵横捭阖!在这如歌的生活中,我成长起来,从教一个区队到教一个队,从指挥一个队到指挥一个团,我也成了干部了!
但有一次,我们副教导员让我教大家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我说这是啥呀,女声的歌,软不拉塌的,拿不出手啊。他说,这是政治工作需要,你教不教?我说不教。他说,那我不给你转正。这下我服了,我的党员预备期可就要满了啊!我这样被吓唬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做单杠三练习,那个立臂上,我就是上不去(虽然我指挥唱歌很有力)。队长说,上不去就不要提干。那是啥当口啊,我一咬牙一闭眼,居然上去了。在那杠上,我眼前是一片星光灿烂。这次当然一样,那就月牙亮晶晶吧。

得敌!
我鼓,我罢,
或泣,或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悲歌虽短,却有英雄的悲壮情怀,其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催人泪下。
刘邦顺应时势,起兵抗秦,入咸阳,败项羽,平叛逆,真如风卷残云,所向披靡。他酣畅的歌声,展现出南征北战的辉煌,抒发了夺得天下的豪迈情怀。这是英雄之歌,胜利之歌!当千古传唱。
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汉武帝时为骑都尉。他以五千步兵和匈奴单于八万骑兵开展激战,因矢尽粮绝,战败投降。那一定是个漆黑的夜晚,风吼叫着,飞沙走石击打着帐篷。老友绝别啊!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而不改其节,其崇高气节名扬四海。而李陵攻打匈奴,战败被迫投降,蒙受了厚厚的耻辱。李陵难抑悲哀之情,放下杯盏,席间起舞,长歌当哭: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这是一曲百感交集的歌。将军孤军深入,万水千山,度越大漠,岂是贪生怕死之徒!面对操守高洁的老友,其悲伤之情,声泪俱下!更何况,老母妻儿已被生性疑忌的汉武帝残忍地杀害了,纵想报恩归汉,已毫无可能。那就用这诀别之歌,倾诉衷肠吧!
这《易水歌》、《垓下歌》、《大风歌》、《别歌》,曲曲动人魂魄,首首憾人心灵,是历史天空中不息的旋律。“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别旧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战争就这样伴随着歌声,给将士们带来多少悲伤和欢欣,痛苦和喜悦。

全队集合!值班员一声口令,全队齐刷刷成连纵队。“今天的队列歌曲比赛,大家有没有信心?”“有!”这是最基本的战前动员形式。部队里大都这样大声问一句,然后等待着响亮的回答,已成定势。抗美援朝期间,我志愿军空四师某部出征前举行誓师大会,朱德、刘亚楼等同志亲临大会,该部队一位领导讲完话,为鼓舞士气,特意站起来向台下喊道:“打败美国鬼子有没有信心?”“有!”。那声音震耳欲聋,如雷声响彻山谷。“有没有决心?”“有!”“有没有孬种?”“有!”又是山响的回答,可紧接着就是一片哄堂大笑。
部队有规定,“三前一路”有歌声。“三前”就是集会前、开饭前、点名前;“一路”指出操训练、开饭、集会的路上。这队列歌曲比赛就是为落实这“一路”的要求。一个队二百多人的队伍,围着营区转着圈地唱,全团都能把营区围起来。那气势,那阵势,叫绝!我带队唱了《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歌是进行曲速度,正合每分钟120步的齐步步速,再说了,《乐记》上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我们刚刚讲了雷锋的故事,大家崇敬雷锋,唱出来就有了背景,那就不一样了。《乐记》上还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那几天正是纪念毛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日子,评委们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果然,我们又获得了冠军。
军歌嘹亮,经常给人以铿锵有力的单面感觉,其实不然。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审查驻京陆海空三军联合演出的歌舞晚会后说:“这台节目激情的太多,抒情的太少了,不要都是一个节奏,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嘛!”很快《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在作者随舰航行三天三夜之后便问世了,而且很快传遍全国。这也说明,军歌的生活来源是军人的作战、训练和感情,兵们自然就乐意歌之舞之操练之了!《真是乐死人》这支活泼欢快的军歌,就是这样产生的。曲作者说,他和词作者杜林中正在部队深入生活,在一次新老兵联欢会上,听到一个新兵叙述他连续3年报名参军的经过,故事生动感人,杜林中当场就写出了歌词,曲作者也用十几分钟就谱好了曲子,很快这首歌便在军营中传唱起来。谁有了高兴的事,比如收到女同学来信,就情不自禁地:“真是乐死人,真是乐死人。”
歌声与自己的心情很贴近,自然就卖力气唱。而歌曲如果跟自己有些关联呢?那唱起来就更加亲切了!1979年中央电视台在我所在的潜艇学校拍摄《潜猎从这里开始》的专题片,其中的插曲叫《走向海洋》,蒋大为唱的,那叫好听,也是红极一时的。那几年每逢开会,我们就唱。因为那片子里有许多我们熟悉的身影和脸庞。只可惜我们没有作为校歌唱下去,这是让我一想起就遗憾万分的事情。

军人与歌声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文化现象。因为,战争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较量,不仅仅是肉体的搏杀,也不仅仅是战略与战术的比拼。所有战争无不是在民族精神、气节和文化上的胜利或失败。因此,战争更多的是精神力量的抗衡和交锋,这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和美国国歌《星条旗》的诞生中窥见一斑。
《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和聂耳于1935年为故事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歌词是田汉遭反动派逮捕前,匆匆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的。聂耳当时也遭反动派的迫害即将赴日本,但他一见这首词,兴奋地一把抢过来:“作曲交给我,我干!”随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到日本后不久,他把歌谱好寄回。歌曲一经影片播放,立刻产生巨大影响,不久传遍全国。而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对这首歌的演唱并录成唱片,更使这首歌传向全世界。至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之后,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改定的国歌歌词。可到了1982年12月4日的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美国国歌,同样诞生于战争年代。19世纪初,当时由于英美两国的利益冲突,形势不断恶化,致使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1812年美国向英国宣战。1814年美军连连失利,英军在新奥尔良城和华盛顿先后取得胜利,又准备进攻巴的尔摩。在这紧要关头,一个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的美国人,为了要救出被英军关押的朋友而去英营做说客,英方扣留了这个美国人。半夜,克伊在敌船上听到战斗打响,却不知谁方取胜,他在焦急中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在晨曦朦胧的光亮中他看到远方飘动着的星条旗,这说明美军守住了阵地!他激动、兴奋,充满了豪情,在信纸上把当时一首流行的《致天上的酒神》曲子重新填词,写下了这首歌曲,第二天就被印成了传单,一星期后印在巴的尔摩报纸上,被广泛传唱。以后就成为庆典时的代国歌。1931年由胡佛总统签字命定此歌为美国国歌。
国歌,往往来自战争,那是一个民族感情的上游,不可以截流的啊!
看《西线无战事》,那些被哄骗到前线去的德国青年,他们奔赴战场时,也唱着歌行进,影片中出现两次这样的情景。我理解,他们也是军人,当然也离不开歌声。只是那不是正义之歌。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有一首《神圣的战争》:“起来,伟大的国家,起来,作决死战!要消灭法西斯强盗,万恶的匪帮……”这首歌的首次演出是在白俄罗斯的火车站的军用列车旁,向正在整装待发的红军战士们演唱的。第一遍唱完,红军战士全体起立,要求再唱。当时,群情激昂,一连唱了五遍,这热烈的场面才告结束。这就是正义之歌的力量!

在军营操练歌声,是一种宣泄,是一种表达,是一种展示。宣泄的是兵们的感情,表达的是兵们的心情,展示的是兵们的风采。早操训练唱“迎着灿烂的朝阳,怀着远大的理想……”;傍晚收操就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走在大街上专门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聚时唱“你来自边疆,他来自内地,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分别时就唱“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还唱“还记得门前那棵树吗,还记得炊事班的饭菜香吗?”有一年学员们毕业会餐,不知谁先唱起了“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引发了一桌人的小合唱,又引发了全饭堂的大合唱,唱着唱着就有人哭了。感情深处的浓浓情意,此时,唯有啤酒和歌声才能比较准确地抒发出来。那就唱着哭,哭着唱吧!
回忆起在军营操练歌声的日子,总是充满了激昂、慷慨、豪迈和厚重感。沉甸甸的,叫人生活起来踏实。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一起诉说心事,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兄弟。战友、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还常常想起我们在艇上的日子吗?神圣神奇的潜艇,让我们知道,原来濳艇人的友情更让人牵挂!过去通讯不发达,许久没有彼此消息,也许我们奔波忙碌,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但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惦记着你。微信让我们慢慢都联系上啦。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们都已老去,即使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带不走我们潜艇人的深厚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