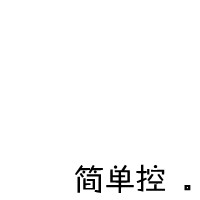(5)(6)/1_Iu5rSSJfbqBiauicSxDkxUhrPBSN0g.gif) 请点击上面的蓝字关注战友之家
请点击上面的蓝字关注战友之家
(5)(6)/2_icJ99EH3pAPTIDUtiaK5gRXN2SQgRQ.jpg)
第三章 二三部门
鱼雷班
(5)(6)/3_X3BPiaxicffn5r58LgtgAUjCpYnJtA.png)
(5)(6)/4_A5YrxSgsicoQ52ibibxyTbbSZWctNw.png)
张毅(1953.8.12~),山东省荣成市(原荣成县)人。1972年12月入伍,曾任155、210潜艇鱼雷兵。1976年9月任219潜艇鱼雷班长。1979年3月退役,任天津航道局第二工程处水手、船队施工记录员。1983年3月,任航标处经济民警、宣传、组织、纪检干事、团委书记。1989年9月,任烟台海事局航标处船队党支部书记、组织人事科科长、机关党支部书记、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2001年6月,任天津海事局烟台航保中心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授中国海事二级监督长衔。2013年9月退休。现居烟台市牟平区。(5)(6)/5_IZVic9BhowQhOUVjrjgKyQXyVh86oA.png)
张毅留给我的印象比较深,高高的个子,有点瘦,走路的时候上身还有点晃。当时艇上有一批荣成、乳山一带的老兵,家乡口音比较重,几年下来,我已经习惯了那种口音,所以对于张毅等新兵的胶东口音,听起来反而感到挺亲切的。我和张毅打交道不多,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因此我说不出更多关于他的故事。
张毅上艇后的第二年,有一天210潜艇在装卸码头装战雷,当雷车被推到艇首时,不知怎么雷车压了张毅的右脚。当时我正在现场,我让人赶快把他送到支队卫生所。记得张毅很坚强,没叫痛,也没哭。在卫生所包好伤脚,他继续上艇按鱼雷兵责任认真工作。2017年11月青岛聚会时,我见到他,提起此事,他说,退役回地方后,经检查,给他评了三等残废。当年毛主席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张毅是个发扬了这种精神的好兵!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不觉己过花甲之年。不知何故,进入老年群体后,经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以前经历过的事情。军旅生涯的6年,虽时间不长,但6年的往事却始终占据着我脑海的大部分空间。那是我上艇的第二天晚饭后,我和于学龙遛弯回来,看见宿舍门前放着一辆脚踏三轮车,那是我们艇当时唯一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刚刷过油漆,鲜亮如新,我俩绕着车子转了几圈。学龙问我:“这车好骑吧?”我说:“我也没骑过,肯定比自行车好骑,因它多一个轮子,稳定性应该很好。”我俩迫不及待地将三轮车推了出来。学龙抢先上了车,我无奈地倚在车后斗边缘上。那车虽然多了一个轮子,可就是不听使唤,东一头西一头,不走直线,还老撞马路牙子。我急了,一把将学龙拽下车,我骑上去。蹬了几步,也是走S型。学龙在后面说:“快一点也许好些。”我听了他的话,加快了速度,果然好了些。可不一会儿就骑得满头大汗。当我掉头往回骑时,因方向打的太急,刹那间车子翻了个底儿朝天,我被甩出车外五六米远。爬起来时,只觉肘关节及膝关节处刺痛难忍,再一看,流了血。从此,我很久没有靠近那辆车。时隔近两年,1975年8月20日,战备装雷,我右脚拇趾被雷车碾压成粉碎性骨折,流了很多血,恰是这辆三轮车载着我,及时把我送进了支队卫生所,得到及时救治。后来又去了舰队医院。伤愈出院以后,有空我便去看看并抚摸一下这辆三轮车,它是与我的青春鲜血有过“亲密接触”的交通工具啊!那是1976年7月底的一天,我艇正在4808厂船坞中突击抢修。下午收工前,老艇长张连忠来了,他把我们几个值更的叫到一起开了个小会。他简单了解了值更人员的安排后,对我们说:台湾及国内外反华势力近来非常猖狂,并伺机对重要的军事目标和重要设施进行爆炸和破坏活动,你们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午夜后更要加强戒备,确保艇和船坞万无一失。下半夜是我的武装更,艇长最后将目光落在了我的脸上。我心知肚明,艇长最担心的就是船坞的那道水密坞门,一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艇长看了我许久,没说什么,最后他放心地走了。午夜,我接班后,习惯性地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子弹上膛,关好保险,用右手紧握着枪把,插进宽松的裤兜里,肩上背了个空枪套。我一刻也不敢懈怠,绕着坞道两侧U型巡逻。那天是个阴天,天气异常闷热,没有一丝风,偌大个船厂安静极了,没有任何声响,只有虫儿的叫声和蚊子发出的嗡嗡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不由得想起前几天发生的恐怖的一幕。一个工人从坞道边缘上摔下去,一命呜呼,白花花的脑浆和鲜红的血液混杂在一起,还有那圆瞪的眼睛,越想越害怕,情不自禁地向曾经停尸的位置多看几眼,这无疑给自己本已绷紧的神经增添了些许恐怖感。大约在下半夜二点左右,当我警惕地巡逻在坞道的南侧时,仿佛听到坞的北端有声响,转身向北看,发现了异常情况:一直照着坞门的探照灯转了个方向,坞门处漆黑一团。我第一反应就是:有情况!心想:真他妈的活见鬼了,三更半夜的,哪来的人呢?为什么把灯光从坞门处移开?……不好,难道老艇长担心的事将要发生?时间不能耽误一分一秒,这时也来不急通知艇内值更人员,只能自己处置了。不容多想,我从裤兜中迅速拔出手枪,同时打开保险,避开明亮处,猫着腰向坞北方向急速走去。当走到距坞门约四五十米处,发现好像有微弱的亮光闪了几闪,毫无疑问,坞门处有情况!继续往前走,好像是一个人,在坞门的吊桥上露出一只脑袋和半个肩膀。距离十米左右,终于看清了,是一个人,蹲在吊桥的二层台阶上,在干什么仍然看不清。我在他的左侧,双手握枪,瞄着那人的脑袋,小声问:“谁,在这干什么?”没有反应,紧接着我大喝一声:“举起手来,我要开枪了!”一场虚惊!当我关上手枪的保险时,发现右手小指在滴汗水。经查问,原来他是4808厂的工人,30多岁,结婚时没房,几个工友帮忙在船坞东北角方向搭了个窝栅,只能睡两个人,点个油炉做点简单的饭菜,用水也是外面提回来的,大小便只能在周边解决。夏天,他怕拉在陆地上臭,就跑到坞门吊桥上排进大海。他怕别人看见不好意思,才把探照灯转了个方向。微弱的光亮是他抽烟发出的余光……嗨,真扫兴!一次充满英雄气概的行动,让一个拉屎的给闹变了味。在我前半生中,最值得回味、最值得留恋的就是我们155、210潜艇这个战斗集体。它是在张连忠艇长为首的一大批老领导、老战友的共同努力下,打造成的一个风清气正、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坚强艇队。这里讲几个老艇长张连忠的故事。我在潜艇装战雷时,不小心脚趾被雷车压伤。养伤期间,不想麻烦战友天天为我打饭,就经常拄着拐到伙房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事,顺便在伙房就餐。有一次,艇长的儿子大刚来码头看电影。大刚那时看上去也就六、七岁的样子,看完电影,晚上在饭堂吃了块馒头。饭后艇长给管理员缴了三两粮票七角钱。要不是我亲眼所见,谁还会相信这是真的?记不清是哪年夏天,我在七舱保养机械。下雨了,升降口因为电工班刚充完电,电缆还没撤走,升降口无法关闭,只能半掩着。当我准备清理地板时,见地面已经湿了,就索性把升降口全打开了。当时雨下得不大,我想利用雨水擦地板。正在这时,老艇长从六舱过来了,抬头看到升降口没关,立马沉下脸问:“张毅,外面下雨,为什么不关升降口?”我说:“正准备清理地板,省得再洒水了。再说他们充电的电缆没收,我也没法关。”“他们没收,你就不能收吗?有你这样保养设备的吗?强词夺理!……”后面他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转身走了,我在升降口下面站了好半天。我心里感到很冤,强忍的泪水“哗”地夺眶而出。过了一会儿,我擦干了眼泪,迅速爬上甲板,不知是哪儿来得那股子劲儿,那么粗的电缆,我硬是一人拉出了舱室。雨渐渐下大了。当我在浮码头上冒雨整理电缆时,突然从舰桥上传来艇长的声音:“张毅,快进舱避避雨,好天再整理,别感冒了。”我抬头看了艇长一眼,这时他的脸也放“晴”了,露出很心疼的样子。但我有个犟脾气,又是在气头上,哪会听他的?我装着没听见似的,一直冒雨将电缆整理好后才返回舱室,并关严了升降口。这时我感到两臂酸酸的。后来我想:多亏被艇长批了一通,使我有机会体验了一下电工兵的工作。电工兵也很辛苦啊!1979年初,那时我已调到219潜艇工作,老艇长在支队当支队长。一年一度的老兵服退工作开始了,天津航道局烟台第二工程处来部队招工,因我有脚伤,单位又离家近,我感觉这活儿挺适合我,就报了名。没想到最后艇上将仅有的一个名额给了别人,让我继续留队。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就壮着胆子去找老艇长。他认真听了我的请求和愿望,第二天就去了支队卫生所找所长了解我的伤情,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跑到舰队,为我单独争取了一个名额。这就是我们的老艇长,身居高位还能为当年手下的一个小兵安排工作,为我忙活了一整天,让我十分感动。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老艇长有一颗爱兵如子的心。第三章 二三部门
鱼雷班
(5)(6)/6_8HFcciaDCBFdFOEC3zy7QicFazkLbg.png)
何忠伦(1955.2~),浙江省奉化市人。1974年12月入伍,1975年11月起任210潜艇鱼雷兵、鱼雷军士长;1981年6月入潜艇学院鱼雷长培训队学习,1983年12月任346潜艇鱼水雷长;1985年9月入大连海军政治学院潜艇政委班学习,1987年11月任潜艇支队政治部组织科正营职干事,1989年11月任238潜艇政委。1994年8月转业到青岛市国家税务局工作。(5)(6)/8_TTCpjP36KgvSYOKof9fgSiaicFHOyw.jpg)
何忠伦当兵比较晚,和我不是一个专业,在艇上接触不多,总的印象是,他比较能吃苦,身上的工作服要比别人脏。具体细节则说不出来。2008年,我编辑老艇纪念册时,他应约写了一篇文章《人生的磨砺》,他所写的故事都是我不知道的。
1974年11月,我入伍来到海军潜艇学校。经过紧张的入伍训练和专业培训,于1975年11月分配到青岛潜艇支队210潜艇任鱼雷兵。210潜艇训练有素且长期担任战备值班。我下决心要在这样一艘战艇上,做一名合格的水兵。上艇一个多月,一天上午,我担任内务更值班,那天的工作是全艇人员专业学习。部队规定,11点30分准时集合吃午饭。11点20分,我吹哨并喊道:“停止学习,打扫卫生。”这时,第一艇长张连忠从艇部出来,走到我跟前说:“小何,作息时间你是怎么安排的?”我立正回答:“11点20分下课,5分钟时间整理内务卫生,5分钟时间集合,11点30分准时吃饭。”张艇长严肃地指出:“工作学习时间至11点25分停止,5分钟时间打扫卫生整理内务,11点30分准时集合吃饭,记住了吗?”“报告艇长!记住了!”我记住了,部队的战斗作风就是靠这样一点一滴养成的;我记住了,要想在210潜艇当一名合格的水兵,就需要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我很快融入了210潜艇这个整体。我用210潜艇的“特殊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出海训练,不管海上风浪多大,晕船多厉害,我和鱼雷班的同志始终坚持在出航的航道上操练发射管,返航的航道上认真保养机械仪器。上艇不到半年,我就完成了基础科目和海上攻击训练科目,独立担任战位值更了。1976年夏季,潜艇进4808厂航行修理。进厂前,王忠和艇长、王学芳政委进行了动员,强调这次厂修目的意义,并对厂修质量提出了要求。接着,部门长王秉祥、军士长于水洋在部门会议上对本部门的厂修任务提出具体要求和措施。通过两次大小动员,我感觉到这次厂修任务艰巨,时间紧、厂修项目多、质量要求高。进厂后,部门长和军士长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鱼雷发射管除锈涂漆,要求除锈必须彻底,涂漆要均匀,不然出厂后,发射管受海水腐蚀会很快生锈。任务接受后,我准备了不少的除锈工具,钻进发射管内。因鱼雷发射管长有8米,内径只有0.57米,除锈和涂漆难度很大,不能站,不能跪,只能以趴、侧、仰三种姿势交替进行。铁锈的粉末溅到脸上、脖子里,和汗水混合在一起,煞得皮肤火辣辣地疼,但我根本顾不上这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经过努力,我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将平时要用两天时间干的活儿干完了,为鱼水雷部门的厂修任务缩短了时间,据说此速度开创了潜艇厂修史上的先例。(5)(6)/10_0sgwuBb4VmWGicUkaVGktlOajWF2uQ.jpg)
1977年春节,使我终身难忘。记得春节前的十来天,我艇突然接到命令,要求把艇上的战备雷卸下来检测,然后再装上艇。身为鱼雷兵,我明白这意味着鱼雷将要长时间地装在艇上了。后来在战备动员大会上得知,我艇将在春节期间出海训练,并担任战备值班,全艇人员停止休假。想到要在海上过年,心情有些激动。人的一生能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过年,令人难忘。但想起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又不免有些失落。大年三十晚上,艇领导叫信号兵通过信号台发出信号:我艇正在值班,全艇官兵向全国人民致以春节问候,祝祖国人民春节快乐!不多时,信号台传来信号:你们辛苦了,祖国人民向你们致敬!全体官兵听到这个消息,心情非常激动,纷纷向《水下战报》投稿表达决心。当晚,正轮到我值锚泊更,眺望陆地上的万家灯火,感慨万千:国泰民安我站岗,我自豪。这次春节海上战备,我部门的同志还完成了“在水下状态重装鱼水雷及战雷检测保养”训练任务,为保证战斗力,提高战备训练水平,探索出一种新的训练方法,受到上级业务部门的认可,支队在本部队推广了这项潜艇科目训练内容。(5)(6)/12_dRFfh4BFEbXlXoLMgRkjXMrHpqf3Mg.jpg)
九、鱼雷兵李玉瑛
(5)(6)/13_owlT3JCFBmdKO2kiaPgT8iahmYge6g.png)
李玉瑛(1954.3.4~),辽宁省葫芦岛市人。1974年12月入伍,曾任210潜艇鱼雷兵。1979年3月退役,在天津石化炼油厂通讯队工作,先后任班长、副队长等职务。2014年退休。
(5)(6)/14_IZVic9BhowQhOUVjrjgKyQXyVh86oA.png)
关于李玉瑛,留在我记忆中的故事不多。当年在艇上,一般同年兵之间的交流比较多,我比他早当五六年兵,又不是一个专业,再加上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善于“广泛团结同志”的人,所以,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交集。
据沈铭回忆:
李玉瑛干活肯出力,待人也特别诚实,我们勤务部门和二三部门床铺紧挨着,和他相处的很好,曾经多次邀请他外出逛街散心。不过他有一个特点,得理不让人,正好当时放映电影《金光大道》,里面有个人物叫“滚刀肉”,那个演员长得和李玉瑛有点像,于是有人就把“滚刀肉”这个外号送给了他。
沈铭说的事情,我隐隐约约有点印象。但我只记得有个人的外号叫“滚刀肉”,却不记得这个外号属于李玉瑛。这次李玉瑛应我之约,为本书写来一篇短文,说到他在潜艇水下航行时到机舱抽烟的事情,这场景我倒是印象深刻。
水下吸烟
李玉瑛
离开部队离开战友已经快40年了,但是对战友的思念和对往昔的回忆却不时浮现在眼前。记得1976年初冬的那次远航,我们艇远航了一个月,虽然时至冬天,但潜艇里的温度还是很高,我当时和鱼雷兵钱泉根还有舰务兵秦玉伦等人在七舱,由于潜艇舱内的温度很高,我们几个人热得都穿着远航背心裤衩工作。
远航期间,潜艇几乎都是在水下航行,只有夜间处理脏物时才能浮出水面。潜艇在水下电机航行时,蓄电池会释放出来氢气,氢气遇到明火就会爆炸。喜欢抽烟的人,不管你有多大的烟瘾,都必须憋着,只有在水下内燃机航行时才能去机舱抽烟。一般情况下,潜艇都是白天用电机航行,晚上在内燃机的“空气筒深度”航行充电。所以大家都盼着内燃机工作的时刻早点来临。
有一次,我到五舱尾部去抽烟,只见那里已经站满了抽烟的人,有水手长田汝勤、鱼雷班长苏功国、无线电兵赵景学等七八个人在那里过烟瘾,一个个抽得那个香啊!我连忙挤过去,一气抽了三支烟,才算过了一次烟瘾。大家不由得感叹:在潜艇上工作,烟民的日子真的不好过呀!
说到水下吸烟,我的眼前马上就会浮现“烟民”们聚在机舱尾部贪婪地吸烟的情景。很多人会一口吸掉半截香烟。是真正的“深呼吸”。
我不吸烟,无法体会“烟民”的烟瘾来了以后怎么忍耐,一口气吸掉半截烟会如何过瘾。不过我有一个体会,在艇内,当香烟的烟雾从面前飘过的时候,那种香味真是好极了,真可谓“沁人心脾”。我曾经向吸烟的战友要过烟,但是自己吸的感觉,远不如闻别人的烟雾飘过时的味道香。我吸过烟之后,嘴里是苦的,很不舒服,这也是我始终没有学会吸烟的原因。
老艇长张连忠当时也吸烟,我在前面写他的那一节曾经说过。
水下启动内燃机属于“水下一级战斗部署”,艇员必须坚守岗位。这个时候,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艇长。他可以在“一级部署”时到各舱检查巡视。他会利用这个机会,到机舱来过过烟瘾。远航期间,每次内燃机启动以后,第一个到机舱抽烟的就是张连忠艇长。他能一气抽两三支烟,等过足了烟瘾,便起身回到三舱,宣布“水下二级战斗部署”。这时,其他“烟民”才能到机舱来。当然也不能大家一起来,否则机舱就会挤满了人,影响操作,一般都是大家根据每人烟瘾的大小自觉分批地来。
我们给“烟民”准备了用罐头盒做的烟灰缸,里面装一点水,以便他们磕烟灰,不会使烟灰被风吹走。等他们抽完烟,我们再把烟灰缸清理干净。烟灰缸的味道很大,不然会污染空气。
正常情况下,潜艇每天晚上都会进行充电,如果遇到敌情,或者恶劣天气,也会两三天充一次电。这种情况下,“烟民”的日子就更难熬了。我们这些不抽烟的人,往往会“幸灾乐祸”。在生活枯燥的日子里,“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娱乐的内容。
段绪明(?~),湖南省新化县人。1976年入伍,曾任210潜艇鱼雷兵,退役后情况不详。(5)(6)/15_IZVic9BhowQhOUVjrjgKyQXyVh86oA.png)
段绪明上艇时,我就离开了艇队,随后我又回艇参加了一次远航,段绪明也参加了。他在这次远航期间,创造了一项奇葩的记录——半个月不拉屎,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40年后,我要写这本书的时候,大家只记得“半个月不拉屎”这件事,却想不起创造这个纪录的人叫什么名字。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才有人想起他的名字段绪明。段绪明是一位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同志。他有四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是1976年远航时,他17天没有大便,仍正常值更并且非常乐观;二是1978年他小臂摔断后,手术植入筷子粗的不锈钢条,一头还露在皮肉外,在恢复到取出钢条的三个月中,仍正常参加工作,从不叫苦叫疼;三是他每到冬天,两手长满了冻疮,流脓淌水,皮破肉烂,惨不忍睹,他却说没事,照常工作训练;四是1976年在4808厂坞修时,他爬发射管除锈出来,见到一舱有一个厨师用的大铝桶盛有淡黄色的液体,以为是茶水,用碗舀起来就喝。其实那液体是我们检修105声纳568分机临时排放的HY-8油(8#航空仪表油),是绝对不含水的特种油。据说让他拉了一次不小的稀。(5)(6)/16_lsMF1cumBc22Rrx8ibiaOW64YzXiaA.png)
(5)(6)/17_9co5sSHYbDECvVXuqWiaML1MWlTflQ.png)
钱泉根(1956.2~),浙江省嘉善县人。1976年2月入伍,曾任210潜艇鱼雷兵,后调至215潜艇工作。钱泉根和段绪明是一年兵,也参加了1976年的那次远航,只是他没有段绪明那么奇葩的经历,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这次看到他发来的照片,才对这个浓眉大眼的新兵有了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这次他应我之约,为本书写下一篇文章《那难忘的潜艇水下生活》。他难忘,别人也难忘。记得那是1976年的冬天,210潜艇要去执行一次远航任务。我这个刚上艇不久的新兵蛋子,因为一个战友生病而得到这次远航的机会,让我兴奋地一整晚都没有睡好。出航之前,艇长王忠和、政委王学芳给我们作远航动员。王艇长对大家说:这次远航训练十分重要,检验210艇全体官兵的政治、军事素养和实战能力的时刻到了!210艇能否成为捍卫祖国海疆的坚强力量,就看这一次的表现了!在那次大会上,各部门负责人汇报了本部门的机械装备情况,还有同志满腔热血表决心。整个动员会严肃而热烈,年经的我热血沸腾,真应了那句豪言壮语:时刻准备着上前线!要知道,当时我们同年兵分到210艇上的一共是21人,但这次参加出航的只有10名!这心里的高兴劲儿,现在想起来都无比自豪。这是210潜艇入列以来的第一次远航,计划时间为一个月。出航那天早晨,我被一声急促的起床哨惊醒,我的动作异常麻利,不到十分钟洗漱完毕,带上早已准备好的远航必需品,集合上艇,备航备潜。我被分配在艇尾七舱,整个舱室有五名同志:鱼雷军士长、一名舰务兵、一名舵信兵和两名鱼雷兵。一切准备完毕,在汽笛声中,我们的潜艇离开码头,向预定的海域驶去……海上的风很大,潜艇左右上下剧烈摇晃,可怜我这个新兵哪见过这场面,一下就蔫菜了,吐了好几回。军士长和老兵们心疼地劝我吃一点东西,实在不行喝点汤也行,不然这一路胃可有的受了!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分,我身体的感觉好多了,但更要命的是睡觉。潜艇上的床铺宽度约50厘米,上下间的距离也只有50厘米,人只能爬进去,还不能自由翻身。我有个毛病,不关灯睡不着。望着别的战友呼呼大睡,不禁感叹:不当兵真不知道其中的艰辛呐!潜艇下潜后,由于舱室气压不断升高,耳朵时常很痛。军士长告诉我,要把嘴巴张开,这样才会好受一些。按照他说的方法一试,果然奏效。我发现值更的同志总不时地拿仪器测量舱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并不时向指挥舱报告。后来我知道了,原来由于潜艇一直在水下航行,没有新鲜的空气进入,全部艇员的氧气都要靠再生药板来供给。再生药板通过化学反应,吸收二氧化碳,产生少量氧气。听说,那些药板很贵,一个舱室用的药板就可换一辆苏联伏尔加汽车呢!因此,必须要时刻监测,绝不能浪费!当我明白了这点之后,但凡轮到我值班时,我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状态,不是测量就是看书,为此还受到领导的表扬。慢慢地适应了海上的生活,我却有些迷茫不知所措。每天的生活非常单调、枯燥、无聊:不能随意走动,脚上时常有浮肿,关节会偶尔疼痛,我们最多的运动是利用管路当单杠,做做引体向上,或者趴在地板上做做俯卧撑,简单活动一下四肢。这种水下生活,对我们艇员来说,无疑是一种体质上的考验、意志上的磨练、性格上的培养。在那段时间里,我最喜欢读我们自办的《水下战报》了。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会把自己写的诗歌啦,日记啦,以及平时搜集的家乡政策啦,等等,拿去投稿,看到自己的文章登上《水下战报》,开心之极!远航生活,最难的就是时间过得慢。甚至连白天还是黑夜都搞不清,只能靠艇上的24小时的时钟来分辨昼与夜,所以每当看到24点时,就会格外高兴:一天又过去了,新的一天开始了!远航期间,淡水也特别紧张,每天限量供给。说实话,我们这些生活在七舱的人,有时还能“开小灶”,多用一点,但是也不能过于讲卫生。反正在同一舱内,看谁都是一个模样,官兵一致的背心、裤衩,有的还光膀子。特别是轮机舱温度高达40多度,噪音很大,个个汗流浃背。所幸我们的舱室温度较低,不少人羡慕我们。轮机兵来7舱上厕所时,总是在我们那多说些话,其实就是为了多舒服几分钟。这次出海,历时一个月。听说要返航了,大家的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喜悦。潜艇终于浮出水面,军士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小钱,我带你去舰桥吸吸新鲜空气!”在舰桥上,迎面吹来的海风让我心旷神怡。看着威武的潜艇,我突然明白了身为一名水兵意味着什么。也许真的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吧,祖国的安宁,海疆的太平就是我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那一刻,我立志做一名合格的兵,做一个大写的人。从那以后,我又出过很多次海,但第一次远航的情景总是那么难以忘记。现在想来,在潜艇上的日子,真的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了。
(5)(6)/18_QZibXnT5LFVE8VKYDfa8HG9JwdFJFA.png)
(5)(6)/19_SRyicpLgnLW6ua5Lneo4MonaMkianQ.jpg)
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我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但是我们一起诉说心事,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兄弟。战友、战友,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吗?还常常想起我们在艇上的日子吗?神圣神奇的潜艇,让我们知道,原来濳艇人的友情更让人牵挂!过去通讯不发达,许久没有彼此消息,也许我们奔波忙碌,很久没有联系过了,但是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惦记着你。微信让我们慢慢都联系上啦。即使过了几十年,我们都已老去,即使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带不走我们潜艇人的深厚感情!
(5)(6)/1_Iu5rSSJfbqBiauicSxDkxUhrPBSN0g.gif) 请点击上面的蓝字关注战友之家
请点击上面的蓝字关注战友之家(5)(6)/2_icJ99EH3pAPTIDUtiaK5gRXN2SQgRQ.jpg)
(5)(6)/3_X3BPiaxicffn5r58LgtgAUjCpYnJtA.png)
(5)(6)/4_A5YrxSgsicoQ52ibibxyTbbSZWctNw.png)
(5)(6)/5_IZVic9BhowQhOUVjrjgKyQXyVh86oA.png)
(5)(6)/6_8HFcciaDCBFdFOEC3zy7QicFazkLbg.png)
(5)(6)/8_TTCpjP36KgvSYOKof9fgSiaicFHOyw.jpg)
(5)(6)/10_0sgwuBb4VmWGicUkaVGktlOajWF2uQ.jpg)
(5)(6)/12_dRFfh4BFEbXlXoLMgRkjXMrHpqf3Mg.jpg)
(5)(6)/13_owlT3JCFBmdKO2kiaPgT8iahmYge6g.png)
(5)(6)/14_IZVic9BhowQhOUVjrjgKyQXyVh86oA.png)
(5)(6)/15_IZVic9BhowQhOUVjrjgKyQXyVh86oA.png)
(5)(6)/16_lsMF1cumBc22Rrx8ibiaOW64YzXiaA.png)
(5)(6)/17_9co5sSHYbDECvVXuqWiaML1MWlTflQ.png)
(5)(6)/18_QZibXnT5LFVE8VKYDfa8HG9JwdFJFA.png)
(5)(6)/19_SRyicpLgnLW6ua5Lneo4MonaMkianQ.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