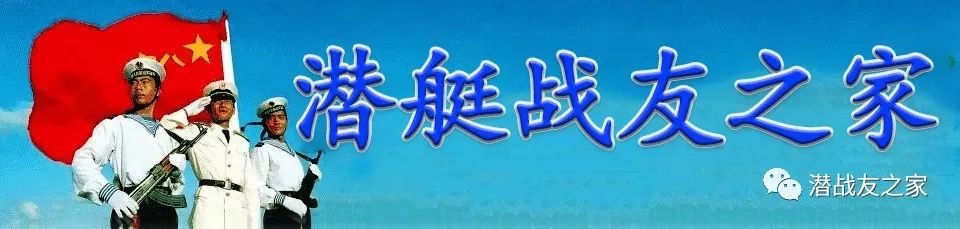

我们的“春晚”
刘俊科
在中央电视台还没有办“春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自己的“春晚”。那时候,多是冬季接兵,个别时候是一年两次接兵,比如一九七六年就是春季和冬季两次,俗称“大七六”“小七六”。冬季兵就会赶上在入伍训练期间过春节。说实话,无论是对于干部还是对于战士,过年,就是“过年关”。因为,新兵来部队的第一个春节,是他们思念亲人最为强烈的时候。而对于干部来说,既要克服自己的思乡之情,还要帮助战士们过好第一个年,就更加是一个“关”了。当指导员的时候,春节来临之前,我就开始布置文艺骨干排练节目。那时候还是人才济济的,吹拉弹唱的都有,组织一台节目还是不难的。难的是要让兵们开心快乐,忘了想家。所以,节目的组织挑选上就得动脑筋。不能刺激了兵们想家的那根敏感的神经。一旦有一个哭的,那就会像风一样哭成一片的。所以,我们的“春晚”是有着使命的。年三十的晚饭都是按惯例会餐,会餐之后就组织我们的“春晚”。有一年的年三十会餐,我到机关开会,会议到了晚饭时间没有结束,我就着急。因为这顿饭是不同平常的,正常情况我是要讲一段话的。但是没有办法,只能等会议结束了。但是,我晚到了大约二十分钟吧,回到饭堂,我们全队都坐在饭堂里,等我回来。队长说:“今天是年夜饭,咱们一个也不能少。更何况是指导员。”我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举起碗,一饮而尽。正在大家尽情享受年夜饭的时候,一个兵满嘴是血的来到我跟前,说是要请假到卫生队,我一问,原来是他用牙齿开啤酒瓶,把瓶子咬破了。我十分紧张,放下碗筷就陪他去了卫生队,好在没有大问题。这个兵叫魏新华,多年以后他来青岛出差,一见面就给了我一个熊抱,热泪盈眶。那时候我们基层没有电视机,我们队好像是一九七八年才有的第一台电视机,还是让一位上海的班长回家走后门买来的。到了看电视的时候,就把电视机放到小操场上,大家坐在小板凳上伸着脖子看。过了几年电视里放日本的《望乡》,我们几个队干也不知道这个片子是个什么内容,就让大家看了。可事有凑巧,我们教导员刘全世那天值班转到了我们队,他看了几眼电视,就火了,大喊着:“给我关了电视!”我们几个队干从队部出来看他还是一脸怒气,就赶紧解散了队伍,把他请到了队部,当然,我们只有老老实实的被骂了。教导员老了,这几年我们在过年前后都要请他吃顿饭,说起此事,也是在笑声里感叹世事变化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了。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我们的“春晚”就更加重要了。当然,还要布置环境,组织游戏。一九八四年的春节,我们队的大部分带兵的干部和班长都抽调到“阅兵大队”,我带着几个班长给大家过年,节目都准备好了,红灯笼也挂起来了,门口也贴上了对联。在开演之前,我们队长孙广山带着到“阅兵大队”集训的干部和班长回来了,他们给我的支持,让我感动不已。其实,我们的“春晚”最出彩的就是官兵同乐。干部们站在台上,或者唱或者舞,有才艺的就展示下,没有才艺哪怕是跑调也亮一下歌喉,台下就会欢欣鼓舞。当然,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站岗的放哨的都换成了我们干部了。后来我到沙岭庄院区当政委,就把我们的“春晚”搬到了大礼堂里,好在有共建单位的支持,节目自然要精彩许多。但是,依然要突出我们的“官兵同乐”,我们“一班人”一块上台,给大家来一个小合唱,每次都是最受欢迎的。陪战士们过年,是对干部素质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官兵感情的一次升华。过了年,到了训练场上,口号震天,虎虎生威。看着,心里就洋溢着满满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