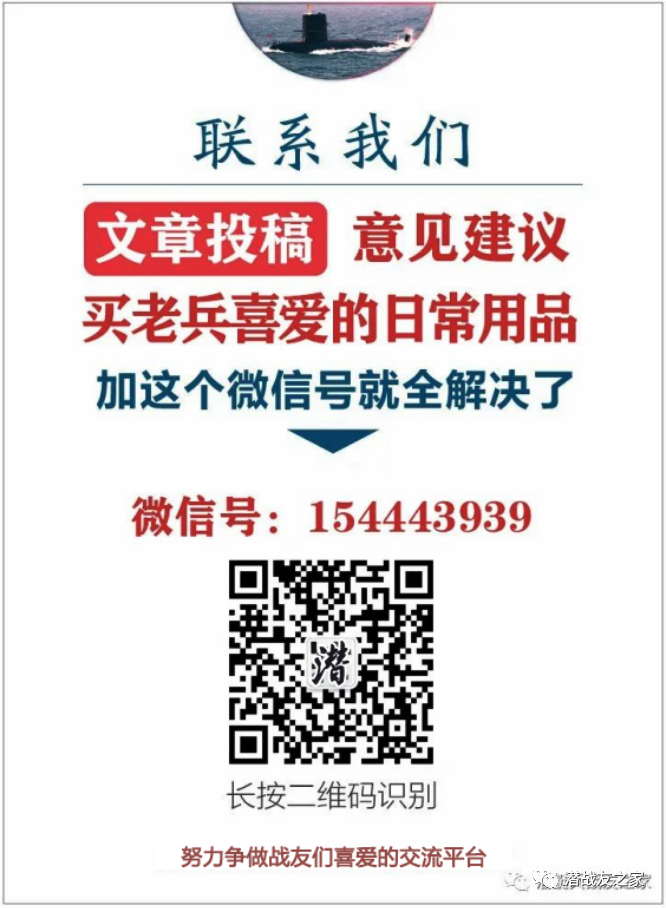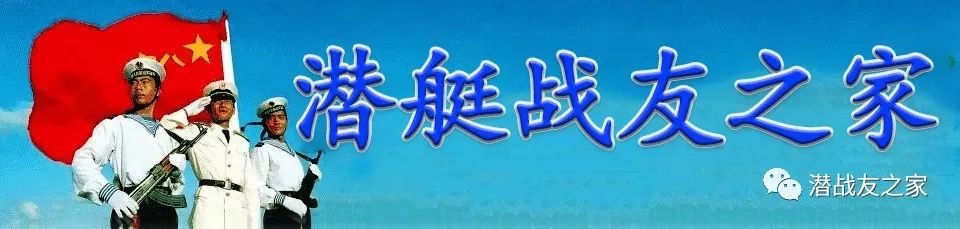

我们的年夜饭
刘俊科

新兵到部队的第一个春节,对于他们而言,就好比是一次过关。这一关安稳顺利地闯过去了,就意味着他们成熟起来了。这有点儿像过去的“弱冠礼”,不仅仅是年龄长大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感情上更加坚韧了。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心理断乳期”,年轻的士兵,刚刚离开校门就走进了军营,他们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就好像婴儿刚刚断乳,精神上的焦虑、不安,像潮水一样,在胸中起伏,只要遇到合适的环境便有可能冲破感情的堤坝,一泻千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当指导员,我们队一名新兵就在春节前不辞而别,我们组织所有带兵的干部和班长到处去找,也没有下落。正在我准备为此写检讨的时候,我接到了他在济南火车站打来的电话,他说“指导员,我现在回去,你还要我吗?”我当即告诉他“我当然要你,而且,既往不咎。”他回来了,是因为在火车上他碰到了一位转业干部,看装束就知道他是新兵,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开导,他在济南下了火车,给我打了电话。他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这件事情,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从那儿开始,时代给我们带兵的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所以,带兵的人,到了过年就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要让新兵们过上一个温馨有意思的年,即使再累,也要把这个年过好。那个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炊事班,放假期间的伙食安排,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尤其是年夜饭,司务长都要一道菜一道菜的把关。 除夕那一天,我们在食堂门口贴上对联,挂上大红灯笼,饭堂里也装饰一新,挂上彩灯,气球。团首长和机关干部也分成若干个小组参加各个学员队的会餐。一般在团首长讲话结束,第一杯酒端起来,整个饭堂就是一声“噢——”,你说这是宣泄也好,你说这是表达也好,反正那一刻,我认为他们过年的心声是明亮的。据说,这是潜艇部队的一个就餐文化,来自于老虎尾潜艇学习队。那时候,因为苏联专家在会餐的时候都要喊一声“乌拉——”,我们的学员就跟着喊一声“乌——”,慢慢地演变到后来的“噢——”。至今为止,凡是老潜艇兵聚餐,你都可以听到这一声荡气回肠的冲天一啸。或者说,你如果在一个场合听到了这一声呐喊,那一准是潜艇兵在一起了。那个年代限酒不禁酒,大家用吃饭的碗倒上啤酒,不论是首长还是士兵,用碗一撞,道一声“过年好!”也是满满的情和爱。当然,现在禁酒也是必要的。 那一年到我们队参加会餐的是政治处主任刘全世,他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工干部,有一年一位南方学兵因为不愿意到分到北方的部队,那么多各级首长做工作他就是不起床,可是,刘全世主任跟他谈了二十分钟,他就自己打了背包出发了。后来,我问过刘主任,他跟我讲了许多经常性思想工作的经验。我后来在多次基层干部的集训中讲过这个例子。记得在我准备休假回家侍候月子的时候,他在营区的路边,跟我谈了那么长时间,有祝福更有嘱咐,至今想起来都是温暖的,这份温暖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而冷却。那次会餐之后,他到了我们队里,跟大家一起做游戏猜谜语。还跟大家说,你们指导员喝多了没有呢?大家只是笑,没有敢说的。他就说,那我试试就知道了。他让我跟他一起数蛤蟆“一个蛤蟆一张嘴,两只耳朵四条腿,扑腾一声跳下水”哈哈,果然,我没有数过六只蛤蟆,大家哄堂大笑,前仰后合。多年以后,我当团政委的时候,每当除夕,我都让机关灶在夜里12点以前煮一锅饺子,我带着几个战士到各个值班岗位去送饺子,包括锅炉房值班的。忘了是哪一年了,我在跟除夕夜里站岗的战士聊天,大概是陪他站了一会儿岗吧。过了好几年,他考回了潜院本科班,我也到了政治部工作。一次我带队出海实习,他自报家门找到我,说是他叫毛书鸿,讲起了当年我来到了他站岗的哨位,说了些啥啥。我哪里记得啊,但是,不记得,依然温馨。那应该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午夜,稀稀落落的鞭炮声还没有停下来,万家灯火渲染着城市的节日气氛,一个老兵一个新兵,在岗哨上交谈着,或许没有宏大的理论慷慨的激动,但一定是亲切而自然的。就从他找到我那天开始,我们建立了联系。此后,每年的除夕,年夜饭的时候,我都能收到来自海疆前哨的那一声问候:“政委过年好!”过年了,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向所有的潜艇新兵问候,祝大家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