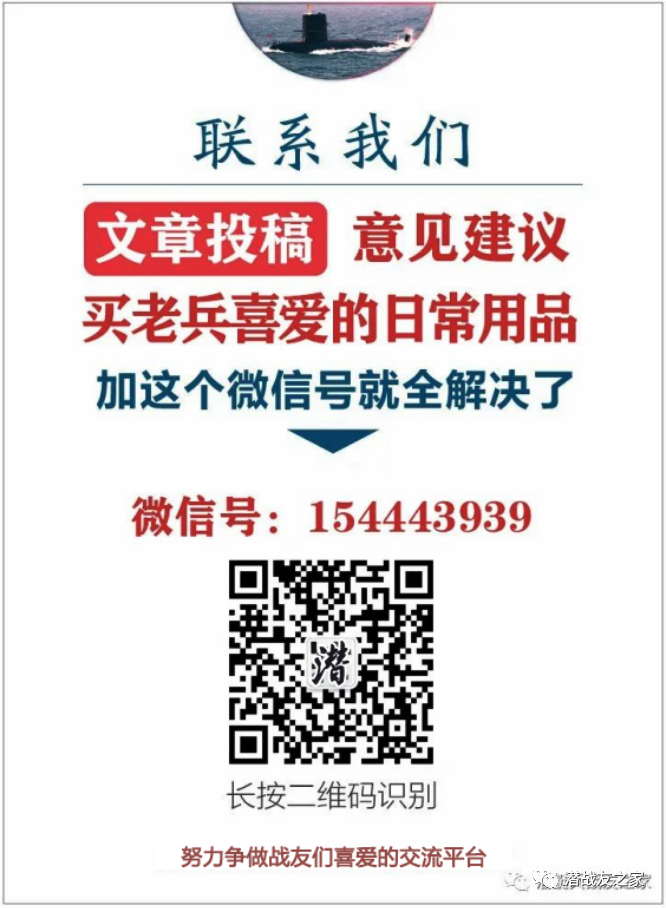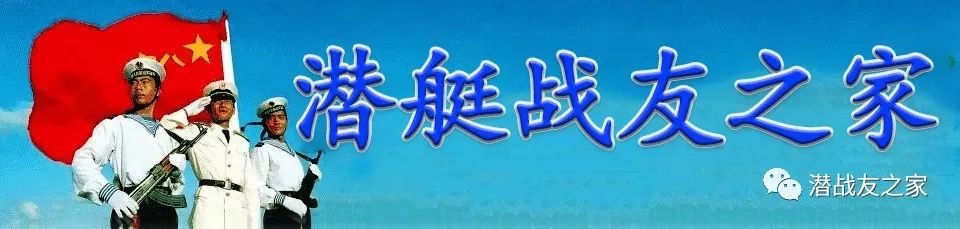

我的水兵帽
刘俊科
1976年的春天,具体说是二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注定成为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从那天开始,几十年的时间里,每次填表,它都会堂而皇之地写在简历栏目的第一行。成为我生命历程的一条起跑线。列车驶进青岛,天已黑透了。接兵的干部说,外面就是大海,我们就挤到车窗前,用尽力气看,可看到的却是一片漆黑。心里渴望的大海,又平添了一层神秘。从沙岭庄火车站下车,我们鱼贯而行。背包在身上七扭八歪的,脚下的声音凌乱不堪。一轮月亮,从故乡跟随我们来到青岛,不离不弃。大沙路的灯光有些昏暗,我们这些潜艇新兵就沿着这条路来到了潜校二大队后来的潜院训练团,开始了我们的军旅生涯。我们的青春开始萌动、蓬勃,跃跃欲试。就好像水兵帽上的黑飘带一样,舞动着理想,飘扬着暖洋洋的阳光和心事。每当写到这个情景,我都会用“青春的森林”来对应那时的我们。但是,1976年我们的水兵帽上没有飘带,是秃的。据说是一位要人在一次到海军某部视察的时候问起过黑飘带的来历,被她定义为“封资修”,就给活生生地剪掉了。“四人帮”倒台之后,黑飘带才又重新在我们的水兵帽上飘扬起来。那个年月我们真的是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崇高和伟大一点儿也不空泛,而是体现在实实落落的具体工作和训练中。我们没有矫情,也不懂得掩饰,争先恐后地表现自己内心的愿望。那个夜晚,我们跟随接兵干部走进训练团。路面崎岖不平,偶尔会踢到石头,打个趔趄。月光如水,我们就趟着月光,哗哗地往前走。这条路也就像一条河,两岸排列着营房。我们被安排在其中的一栋房子里,这便是我们的中队。中队长姓马,他教我们怎么样戴水兵帽。我有幸被他叫到队前,当了一回模特。水兵帽是左高右低,队长说,左边要离眉毛两指宽,右边离眉毛一指宽。这恰到好处的倾斜,让我们年轻的脸多了些灵气,看起来真的挺精神。队长在以后的时间里还教会了我们许多。一次中午饭后,有人丢到泔水桶里一块馒头,他叫值班员全体集合,夏天的阳光直接照在我们的水兵帽上,晒得结实。我们知道出事了,少不了受罚。可他从泔水桶里捞出那块馒头,一边吃一边说:“不能浪费粮食”。好像在说着家常。我们都低下了头,不管是哪个所为,我们都感到了无地自容。队长转业回河北安置,我和战友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家。那是冬天,下着雪,雪大如席,覆盖着万物和我们的心情。他穿一身褪下领章帽徽的戎装,火车开动的一刹那,在车门处,他举手敬礼。那个车门像个相框,多少年就这样挂在我记忆的墙上。之前听说了许多关于让他转业的说法,而不管是什么说法,我们都难以接受。回去的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听着脚踩在雪上吱嘎吱嘎的响。这座院落“文革”期间停止了它的使命,刚刚恢复两年,原来的院落被分割的七零八落,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显得有些有些破落。荒草茂盛,石头嶙峋,到处坑坑洼洼。我们开始除草修路,一边训练一边劳动,有点儿“三五九”旅的劲头。最艰难的是我们开始修大操场,那是一片乱山岗子,我们是用最原始的工具一镐一锹地挖。十字镐头下去,只是一个白点,好像牙齿咬在冰上,仅仅是划出一点痕迹而已。就这样我们一厘米一厘米地挖山不止。后来可以打眼放炮了,炸开的石头我们用小车推也用肩膀扛。有的时候挑灯夜战,工地上人车穿梭,小推车是铁的车架和车斗,空车的时候哐哐直响,整个工地车声鼎沸。副团长站在高处用小喇叭指挥着,像打仗一样。几年时间,一茬茬的潜艇兵用在校学习的业余时间,多数是周日和晚上时间,靠车推肩扛,修成了一个标准的大操场。团长挥毫题字“训练场”。多年以后,这个操场已经是塑胶跑道了,但是我看到那“训练场”三个字依然在主席台后面的墙壁上煜煜生辉。我们当然注意到了院子里的一艘潜艇的部分艇体。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队干部也从不跟我们讲,我们还在它的旁边照相留念呢。后来我们还是知道了,那是418潜艇,是在1959年12月1日于舟山海域的一次反潜演习中失事的一艘M级潜艇。我无意在这里叙述它失事和艇员们壮烈牺牲的过程。多年以后,我曾几次带学员到舟山418烈士陵园扫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亲笔题词:“海军1385部队遇难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在陵园中央。而当地政府的《重茸海军烈士墓志》,给我留下了刻骨的印象,抄录在此,以慰英灵,以励来者。己亥(1959)岁暮,海军418潜艇38名官兵英勇牺牲,天人恸悼。乃择陵舟山,立碑定海。齐高天之寥廓,豪气如虹;共海水之蔚蓝,热血化碧。惊涛拍岸,呼吸可闻;繁星在天,目光可接。夫生死或然也,生作人杰,死为海魂,放缆舟山之舟,扬旗定海之海,肩披碧波,带系长风,屏落东南,翊卫国门,以壮乎哉!昔日甲午一战,百年蒙耻,而今中国编队,远航寰球。荣辱之间,端在海权;存亡之道,制海为先。为不忘前史,昭示后世,秉承海军之关心,特重修陵墓,更葺丰碑。俯瞰千岛城郭,日新月异指示万里航程,继往开来。烈士捐躯,虽死犹生。制海强军,舍我其谁?往者未竟之志,来者当知奋勉也。长眠于此陵园的烈士中有我战友张欣的父亲,每次去,我都特意到那个墓前,久久凝视。看一眼照片,想一下张欣,想一下张欣,再看一眼照片,不胜感慨。我见过时任国防部长的迟浩田写给张欣的条幅:“子承父业”,字体苍劲,饱含情愫。一代一代潜艇人前赴后继,为强大的海防奉献着。418艇唯一成功脱险出水的王法全,在抢救过程中,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自打来电话,命令:“组织力量全力抢救,谁也不能让他死。谁给弄死了谁负责!”每次提到这个细节,我都有作为后来者的激动。王法全在身体恢复后,被安排到潜艇士兵学校担任潜艇损害管制教研室实验室主任。后来在天津塘沽海军干休所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418潜艇的艇体的一部分竖立在潜水训练场地,供学员逃生训练至今。这么多年了,我总觉得这其中隐含着一种历史感,甚至是悲壮感。在我们反复的下潜上浮中铸就了光荣与梦想。潜艇兵入伍体检的时候,到最后一次复查,主检医生要在体检表上写下两个字:“合潜”。不明就里的以为是潜水员合格了,其实这就是潜艇兵合格了。但是,这个“合潜”却有意无意地包含了潜水合格的意思。因为潜艇官兵是要学会潜水的,就好像飞行员要学会跳伞一样,是必须的。潜水训练我们用的装具是“28”型呼吸器,看上去挺简单的装具,却是当时潜艇官兵逃生的必备也是唯一的装具。逃生,这个严峻的词,开始我们是极其避讳的,好像一说逃生就带有耻辱感。直到教员在课堂上大声说出“逃生训练”这个词,在他的不断反复中,我们才接受了这个概念。然而,从心理层面接受这个词,还是通过严格的训练之后。当然还有那些“万一”发生了的事实。每一名潜艇兵都要经过严格的逃生训练,从潜一米、三米到潜十米……,从爬发射管到闸套出水,我们佩戴着“28”型呼吸器,在水里游刃有余,畅快淋漓。但训练刚开始,我们紧张、担心,甚至恐惧,有的不敢钻发射管,有的不敢进闸套。有的钻进发射管了,可刚刚关上后盖,就“当当当”敲击紧急信号,无奈,教员只好打开后盖,问:“怎么了?”回答:“报告教员,我想上厕所!”大家就把笑声使劲憋着。紧张是难免的,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更何况有的还是“旱鸭子”。我就见到过新兵站在发射管前,小便从泳裤流出来的。但是,我们都在训练中长大了,成为合格的潜艇兵。学会潜水,要学会用嘴呼吸,是只用嘴呼吸。最开始,我们就在脸盆里练习,咬上呼吸阀,把头埋进水里,只要你用鼻子呼吸,就会呛到。到了戴上呼吸器 ,潜到水里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安全绳,自己都能够听到心脏的跳动。几次下来,就该爬发射管了。发射管是用来发射鱼雷的,到了“逃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钢铁通道。几个人一组爬进去,管子的前盖是关着的,人进去以后要关闭后盖,之后就是注水加压,直到内外压力一致了,才打开前盖,里面的人依次从管子里钻到水池里浮出,才算是完成了一次训练。管子里漆黑漆黑的,水进来的时候,你会感到十分无助,这时候需要强大的内心力量做支撑,不然,你就会心慌意乱。坚持不住就会敲击管壁,只要有人敲击,就必须停止训练。爬管训练,不仅是练技术,更是练胆量练意志力。一生中有过这样的训练,你的脑海里就不会有害怕的概念了。后来的工作生活中,只要碰到“潜”字,我就会想到那一池碧水,或者那一管漆黑。比如一看到“潜意识”这个词,我就在我的潜意识里看到自己在潜水池里的样子,潜水帽里的眼神,有些神秘并充满警觉。我在机关工作的时候,曾经到潜水教研室总结过“十万人次无事故”的经验,现在,早就“百万人次无事故”了。这个世界级的记录,包含了一代代潜水教员和队干部的心血。人们习惯称呼潜艇为“水下蛟龙”,是因为我们驾蓝鲸驰骋大洋,也是因为我们可以潜行碧波之中。当然,但愿“28”型呼吸器,永远只是我们的训练器材。有备,无患。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里说过:“一个人命中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生活的使命。”我们那些队干部和教员就是有着使命担当的人。身穿水兵服的我们,虽然不是人生中年富力强的时候,但是,我们也明白了我们的使命,而且不是朦胧的,是清晰的。我们是第十四期潜艇兵。后来就改“期”为“级”了,哪一年就叫哪一级。我是说,从这个院落里走向海疆前哨的潜艇兵,可以用“千千万万”来概括了。院史馆里有一排将军的照片,他们都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员。当年他们也是带着水兵帽,在这个院落里学习训练,摸爬滚打。有一年我到某基地参观,那条艇的艇长叫我刘指导员,我脱口就叫出了他的名字,我俩都激动不已。他还记得我让他们写日记的细节,一一道来,好像在历史的沉沙里打捞出一粒粒记忆的金子,在我们面前闪闪发光。后来他当了将军,我由衷地感到骄傲。当然,大多数潜艇新兵是在钢铁蓝鲸上默默奉献着。他们中有的在训练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每每想起他们带着水兵帽的清纯的脸庞,就不禁潸然泪下。有一次带队海上实习,经过某失事潜艇曾经的阵地,我和几位带队干部,站在后甲板上,面向长长的航迹低头默哀,泪眼婆娑几近哽咽。那航迹泛起的白浪花,层层叠叠,远处的灭了,近处的又是一片怒放。还记得有一年在为一位在游泳训练中牺牲的新兵送行时,我泪流满面,地方来的一位干部问我:“你跟他的感情很深啊。”我说:“我并不熟悉他。”我知道他很难理解这种感情。我也感到对这种军人之间的大爱,解释起来是很困难的,索性就让他一脸茫然吧。伍尔夫说:“过去总是美好的,因为一个人从来都意识不到当时的情绪;它后来扩展开来,因此我们只对过去,而非现在,拥有完整的情绪。”在一个秋天,我们几位战友到河北看望老队长。华北平原,秋色分明,递进着时间。大地庄重,河流安泰。老队长还穿着老式的旧军装,一身海军蓝,不再挺拔。他坐在沙发上,沙发的旁边是一把轮椅。我们这些当年的水兵给他敬礼,他举起了颤巍巍的右手,给我们还礼。我想到了他在列车上给我们敬礼的那一幕,两次敬礼,暌隔三十年!在青春年华,我们拥有一顶水兵帽,那水兵帽左高右低着戴,彰显出水兵的机智和刚毅。迎着海风,黑飘带飞舞起来,那是大海最美的时候,也是最有意味的时候。我当指导员的时候,带着新兵到沙岭庄的海滩上去看海,他们连鞋子都顾不上脱就高喊着向大海奔去。天生的水兵啊,对大海有着近乎天然的热爱!在沙滩上,他们把水兵帽抛向空中,瓦蓝的天空下,水兵帽旋转着,黑飘带像一双双翅膀飞翔起来。我把这一幕定格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海天之间,有千千万万潜艇兵的名字像一部大片的字幕一样,从他们曾经战斗过或正在战斗着的大洋深处飞跃而出,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