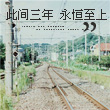文/刘善兴
面包车驶进山坳里一座绿树掩映花草繁茂的幽静小院。
郭叔叔说,咱们下车看看水井。从水泥围沿的井口往下看,黑洞洞深不见底。郭叔叔说,你爸在这儿的时候,葫芦港内没有淡水,淡水要从十几里外的水库引过来,每天定时放一阵儿。每个艇队砌一个水泥池子储备淡水。家属区更热闹,家家发一个大水缸,放水的时候,男女老少盆盆罐罐齐上阵,接满一缸黄泥汤,沉淀后还得节约着用……后来,家属工厂要办酒厂,我下决心找水源,在葫芦港内外打了几十个一百多米的深窟窿,总算找到了甜水层,把全港的吃水问题彻底解决了。这水质,好着呢,我们生产的“金葫芦”牌米酒很畅销,靠的就是这水!
父亲般的老兵,脸上洋溢着自豪。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需要,首先是空气,其次是水。这个水源,是葫芦港的生命之源,战斗力之源,我能够理解,郭明亮厂长首先让我看水井的意图。这是他军旅生涯的得意之笔。
今天刚刚吃过早饭,郭明亮厂长就开着面包车来接我了。
我给他敬了一个军礼,坐到副驾驶位置。想说点儿什么,竟然一时语塞,心底莫名飘来一缕凄惘的感觉:这个年纪的军人,应该是大校或将军级别的首长,而他今年五十多岁了,仍然是个兵。父亲般的老兵今天特意穿起了军装,上白下蓝夏常服,肩上扛着六级士官的肩章,中等个子,紫红色脸膛写满沧桑,神色庄重。面对他的庄重,我油然而生敬意,很亲近很温馨的那种敬意,心底莫名的凄惘逐渐被肃然取代。
他用父辈般的眼神儿打量着我说,好啊,真快啊!马副主任让我接记者采访,又说是童建国的女儿,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你出生那天,是我开车接的,这不,今天又来接你采访,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葫芦港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叔叔,听说您平时一般不穿军装,是吗?话一出口,我自己暗暗诧然,按照事先拟定的采访提纲,并没有准备问这个问题呀?
是的。到底是记者,人没见面,连我平时爱穿工作服的习惯都知道了。原因嘛,很简单,我虽说是综合家属工厂厂长,正式编制还是岸勤部修理所修理班班长,我儿子郭晓涛是汽车班班长,父子俩同在一个单位。有时,穿着军装和儿子走个对面,自己心里也觉得蛮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就尽量不穿。能看得出,六级士官的坦诚写在他的脸上。
郭叔叔,您这般年纪,在支队,人们是怎么称呼您呢?在父亲般的老兵面前,我不想让采访那么正式,想很随意进入状态。
叫我老郭。钟支队长、支队政委,司、政、后、装几大部的领导都是这么称呼。家属们都叫我郭厂长,比较熟悉的人叫我郭老兵,或叫老班长。倒是有几个兵私下里喊叔叔,就是我儿子班里的战士,不叫儿子不答应!说到这里,六级士官爽朗地笑了笑,又说,我开车带你到几个车间,想采访什么,随便问,咱们边走边聊,真的在办公室拉开架势谈,我也说不出啥东西。我这人,一辈子就是干活的命!
好的。我答应着,又问,曾经听爸爸说过,当年葫芦港比较艰苦,不知道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
现在的葫芦港和过去相比,变化简直太大了!郭叔叔启动汽车,缓慢行驶着,若有所思地说,那年我从新兵队分配到葫芦港,听说是到新中国海军当时最先进的潜艇部队当兵,别提多高兴了。可是,交通艇一靠上码头,心里就凉了半截:什么新中国海军最先进的潜艇部队,分明是世界上最简陋的军港!映入眼帘的水兵宿舍、大食堂、机关办公楼、大礼堂、招待所、医疗所、家属宿舍等等,一律是青砖青瓦的平房或两层简易楼房,石料砌基,砖木结构。有的,还不如我们老家农村的房子。
听着郭叔叔的回忆,爸爸影集里的一些照片,在我脑子里叠印出来。
看了水井,就去不远处的酿酒厂参观。规模不大,却管理有序,装酒的流水线上,家属工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然后,又去同在一个大院里的副食品和保险柜厂。
郭叔叔介绍说,军港建成初期,出港没有等级公路,通县城只有一条砂石路。县城的规模是“一条马路百米长,几个路灯全照亮”,和一个渔村差不多!没有面包车、大轿车、救护车,日常必备的专用车辆开始都没有,去火车站接人,去医院看病,一律是解放牌卡车,晴天一身土,下雨拉上篷布,几十公里山路上,总见有家属孩子晕车呕吐,鼻涕眼泪一把长。没有固定的副食供应点。听老兵说,有一年潜艇远航,岸勤部食堂科绞尽脑汁才弄到一筐鸡蛋。没有学校。军港的孩子们到附近山村小学就读,民办教师讲数学题竟弄出圆的半径比周长还要长的笑话,整整十年,葫芦港的孩子没有出一个大学生! 没有幼儿园。要说有也和没有差不多。三间房子、两个阿姨、一台锅灶。啥玩具也没有。没有木马,没有滑梯,更没有钢琴,开始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只有几个布娃娃。每个孩子自带两个饭盒,一盒生米、一盒熟菜。中午,阿姨把生米蒸熟,熟菜温热,照看孩子们吃下去,别磕着碰着,这一天就算完事儿啦。……你想想,就这条件,在城市工作的军官家属,谁愿意来呀?农村籍军官家属随了军,也没有工作,眼巴巴地吃丈夫的工资。那些个年,让干部安心,拴心留人是个大问题,支队首长着急呀!
您说的这些情况,就是家属工厂筹建、发展的原因吧?我插话。
是这样的。郭叔叔说,家属工厂从办石料厂起步。当年,军港在建设中,石料需求量大。一把锤子、一副手套、一个小马扎,军嫂们,来上班吧。不管是首长夫人还是军官太太,不论在老家是干部、教师、工人还是医生、护士、售货员,为了爱情,为了丈夫,为了不再过牛郎织女的日子,军嫂们只好把无奈、委屈和锤子一起举起,狠狠砸下,不少人还泪洒石料场呢……家属工厂年年入不敷出,工资低廉,没有技术含量啊!支队首长找我谈话,说老郭,你把家属工厂接下来吧,反正没有编制,你就是厂长。你要想办法搞点技术项目,总不能让半边天们总敲石子吧!我说,行。这一答应,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先后办起了副食品厂、保险柜厂、酿酒厂,后来在家属工厂前面加上了综合两个字,可还是没有编制,我还是厂长,看来想撒手也甩不掉了……面似木讷的郭叔叔,其实语言表达蛮生动的。
采访前,从相关背景材料上看到,六级士官郭明亮在葫芦港的位置和贡献,相当于支队政委助理——综合家属工厂安置了部队所有随军后“失业”的干部、士官家属,每年按国家政策依法纳税后,创造的利润,给每一个职工缴足“三险”,工资还不低于当地企业的一般水平。因此,支队长钟大魁将军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说,大家不要小瞧家属工厂这点不起眼儿的收入,郭明亮把这一摊子玩转了,干部的思想工作就少了一半儿。身为厂长,郭明亮十几年来天南海北出差联系业务,火车上一律是面包、方便面、矿泉水,舍不得到餐车就餐,舍不得坐卧铺,找当地最差的旅馆住。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咱是战士,摆不起什么谱儿,军嫂们辛辛苦苦挣点钱不容易!
跟随郭叔叔在车间参观,听着他的介绍,作为葫芦港的孩子,历史的隔膜使我难以理解:我的那些描绘军港建设蓝图的父辈们,当初为什么把现代化的军港建设成那个样子?
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家穷呀?在简陋的厂长办公室坐下,我问郭叔叔。
不仅仅是因为穷,现在看来是个建设理念问题。郭叔叔说,葫芦港建设始于上世纪中期,当时国防国际形势紧张,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山、散、洞”,立足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你想嘛,马上要准备打大仗啦,甚至要准备打核战争,军港建设从决策、勘察、设计到施工,都贯彻了一个思路:准备打仗是第一位的,生活设施是第二位的。潜艇有码头靠,艇员有房子住,就比老红军雪山草地露宿,比老八路钻青纱帐,条件好多啦。当时的人就是这么想的。这和后来逐步清晰的建设深蓝海军、建设现代化军港的理念,完全不一样。当然了,如今的形势任务都不一样了。
这么多年了,您一定有过退伍的机会,一定有过比当战士更好的选择,您为什么没有离开,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种坚守?我把采访引向主题。
需要和感情。郭叔叔的回答显得胸有成竹,他真挚地说,领导信任咱,咱不能辜负领导。开始,我在汽车排,领导看我修车技术不错,把我调到修理所。好几次,年底退伍名单里都有我,我也准备走,临行前潜艇机械出现故障,我去协助修理,手到病除。支队首长发话,郭明亮今年不能走。后来到了家属工厂,就更没有机会走了。家属随军那年,我回去搬家,一位开机修厂的老同学说,我这里就缺你这样的技术高手,回来一起干吧,算你入干股,我这厂子的资产有你一半!把家搬到海边那个山沟里,有啥意思!说实话,我也动过走的心思,又一想,咱是战士,又是党员,组织上没有安排咱退伍,家属工厂也需要咱,个人咋好意思开口呢?于是,一狠心把家属搬过来了。后来,儿子当了兵,我把儿子也调过来了,咱也来个“献了终身献子孙”吧……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慢慢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就像葫芦港,一呆二十多年了,习惯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再干几年就该退休了,现在哪里也不想去了……
和郭厂长交谈后,我又召集职工开了一个座谈会。职工们讲起这位士兵厂长的故事,生动而感人。在这位普普通通的父亲般的老兵身上,代表战士底色中最可敬、最纯真、最亮丽的那些色素,放射着异彩,在我心底掀动波澜。
郭叔叔邀请我在厂内用餐,并说餐后开车送我回去,我婉辞了。
回到招待所,开始琢磨起新闻的主题——历史。时代。使命。责任。生活。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很庄重的沉甸甸的字眼儿,一股脑儿地在我脑子里轮番蹦蹦跳跳起来。思绪,剪不断,理还乱。以《父亲般的老兵》为题写一篇人物专访,该从哪里下笔呢?
跌入新闻构思中的思绪,痛苦着也快乐着。

“西沪港战友之家”欢迎广大战友们踊跃投稿,来稿形式不限,短文、小说、诗歌、视频、图片等均可,可通过如下方式发送:
1.发到邮箱:154443939@qq.com;
2.登录“西沪港战友之家”论坛(bbs.xhgzy.cn)发帖;
3.发到微信:154443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