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海鸥飞不到的地方 《升起潜望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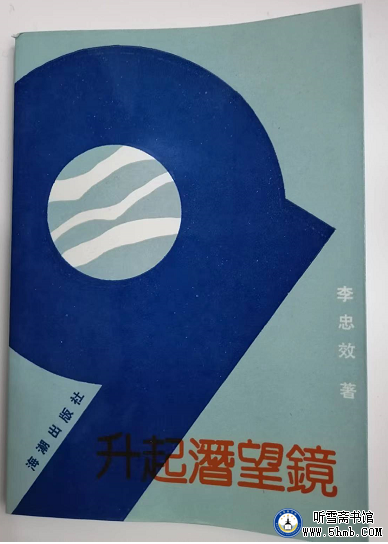
海鸥飞不到的地方
那个地方我没去过。中国太大,没去过的地方太多。我说的这个地方是在横跨长江的一个省份靠江北的一片土丘林林的山窝窝里。
那地方交通不太方便,不通火车,轮船自然也开不去,从江岸一个小城开到那地方县府的汽车据说要一整天。不通汽车的地盘自然不会小。那地方的人不大关心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也不大关心那地方的事情。从那里出来的人会感到对外面的世界不适应,从外面进去的人会觉得那里的气氛不协调。那地方的人不大爱受清规戒律的限制,也没有太多的传统式的观念。用一个时下十分流行的说法,就是活得洒脱。那一年从省城下去一大群被称作知识青年的男男女女,没过多久,女的都跑了,不再回去,而男的却留了下来。虽然后来知青大返城的时候男的也走了,却都十分恋恋不舍。别看那地方偏僻,又穷,男人都丑,那地方的女子却都水灵,迷人,看在眼里拔不出,装在心里放不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当然这都是听说。是我们艇上的一个水兵对我说的。他叫老木。不是真名,是外号。他当兵的时候还不到二十,人却像三十还多。他会点木匠手艺,艇员宿舍的窗子坏了,地板坏了或者厕所门坏了,都是他修。还修得挺不错。有一次一个老兵拍着他的肩膀表扬他:手艺不错,像个老木匠。他咧嘴一笑,满脸的褶子。大概就是从那天开始,有人对他以老木相称了。一来二去,人们竟不习惯叫他的名字,几乎忘记了他的名字。本来艇上不准起外号,可是有一天,艇长竟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叫了一声老木。而且大家--包括艇长和老木在内――竞浑然不知。
老木说他们那地方过去从来没去招过兵。连陆军也没招过。那年不知怎么一下去了那么多招兵的人,陆海空三军都有。他也不知当什么军好,心想只要能验上,穿什么军装都行。结果真就验上了,还是海军!接到通知书那天,他高兴得一晚上没让老婆睡觉。他说,我就要走了,好几年不能回来,今晚上让你好好过过瘾。――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我们俩关系不错,他什么话都和我说。
前面说过,他们那地方的人不大爱受清规戒律的限制,在大力提倡晚婚晚恋晚育的年头,他们那里十七八岁的小毛孩照样结婚生崽当爸爸妈妈。他十九岁结的婚,已经是晚婚了。他一开始学的是舵信专业,就是操舵和收发信号。舵有方向舵和升降舵,信号有灯光信号和手旗信号。他的档案上写的是初中文化,可他居然不会汉语拼音。而信号兵不懂拼音是绝对干不了的,现学他又记不住,于是只好让他改行。别的专业都挺复杂,只有厨师简单。潜艇用的是电灶,只需扭动开关就可做饭。坏了有人修。他挺高兴,就干了厨师。他的厨房和我们的机舱紧挨着,只隔一道防水门。每次出海,只要我不当更又没别的事,我都去帮厨。所以我们俩关系不错。
他一般没什么心思,能吃能睡。那时候除了“红宝书”没别的什么书可读,我们偶尔找来一些“禁书”掖掖藏藏地传着看,他从来不闻不问。唯一的爱好是看人下棋。他能连着一声不吭地看一天,却从没见他和谁下过。当了半年的厨师,他的脸上丰润起来,褶子好像也少了一些。我们都催他照张像邮回去给老婆看看,他真的就去照了一张,还上了彩,嘴咧得像扇瓢。照片还没邮走,他收到家里一封信,接着脸上就没了笑模样。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不说话,默默地把信递给我看。信是他父亲写来的,说他老婆在家里和别人睡觉,那意思是他们现在是体面人家,不能对这样的事情置若罔闻,希望他能回去处理一下。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怎么办?我能回去么?”他满脸的沮丧和悲哀。
按规定义务兵服役期满才能探家,可他的情况毕竟特殊。我把他的信拿给艇长和政委看,他们两个商量了一下,决定给他一个星期的假。临行前政委又找他作了交代: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要勇敢、坚定、沉着。特别是最后一点,沉着。一定不要感情用事。如果需要部队派人帮助解决,立刻来个电报。假期不够,可以适当延长几天,你自己掌握。他点头应着,阴着脸走了。
他走后,政委一连几天焦虑不安,对我说:“如果来电报,就派你去。”我点了头,他又说,“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我理解政委的心,一旦出点什么事,我们艇的“四好标兵”就泡汤了。当时支队政治部派了一个科长一个干事正在写我们艇的典型材料,准备参加舰队的四好连队代表大会,有消息说我们艇有希望当标兵。
一星期之后,老木回来了,满面春风,不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倒像是刚刚渡完蜜月。我不由得都长出了一口气。
“事情处理完了?”没人的时候,我问他。“处理完了。”
“怎么处理的?”
“我把他老婆给搞了!”
我顿时目瞪口呆。他却有点洋洋得意。我对他的关心和同情一下子荡然殆尽。我拍拍他的肩膀,终于什么也没说出来。(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
踩一下[0]

顶一下[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