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机电部门 电工班(2)《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2)
六、电工军士长孙元明
孙元明(1950.3.17~),江苏省如皋县人。1969年2月入伍,1969年4月上艇,1971年任127潜艇电工班长,1974年任155潜艇电工军士长,1978年任210潜艇动力长;1978年10月任213潜艇副政委;1983年入大连海军政治学院潜艇政委班学习,1985年任346潜艇副政委,1985年8月任217潜艇政委,1992年任402核潜艇政委。1996年转业至青岛市广播电视局组织人事处工作,1999年任青岛市广播电视局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
我和孙元明的关系有点不一般,因为我们两个曾是“一帮一,一对红”。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部队流行“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现在回想起来,无非是老兵帮新兵,好兵帮差兵,最终达到“一对红”的目的。孙元明是1969年2月当兵,我是1969年12月当兵。在部队,多当一天兵也是老兵,我自然是他帮带的对象了。
可能有人会问:你是轮机兵,他是电工兵,你们不是一个专业啊!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同属于一个战位:5战6。二级战斗部署,我们分更看大轴。
我们这种“一帮一,一对红”关系大约持续了一年多,“林彪事件”以后,“五好战士”、“四好连队”活动统统停止,好像是“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也是在那个时候中止的。
孙元明的眼睛很大,大约是他思考问题时候精力集中,目光专注,韩芳润觉得他在“发呆”,于是送他一个外号——“小呆瓜”。我们上艇的时候,老兵已经在这样叫他了。
其实,“呆瓜”不呆,那个脑袋瓜精明着呢!
1973年夏天,155潜艇从武汉接回来以后,电工班很快发现二、四舱的两组电池放电不均的问题。每次充完电,第二天就出现二、四舱电池比重不一样的现象,充电一次很快就用完了。孙元明当时是电工班长,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他。当时一上艇,他就要下到电池室去看看,晚上睡觉也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近一个多月反复耐心细致的查看,终于发现电池的中线接错了,本应接在电池的负极,却接在了正极上,结果使一分为二的半组电池不均衡了,半组多了一块,另半组少了一块,造成半组电压高,半组电压低,形成回流循环放电。后来武汉海军工程学院的老师指出:如果时间长了,不仅电池的电会很快放完,而且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孙元明及时发现了问题,不仅保证了电池的正常使用,还给国家挽回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我记得,艇长张连忠曾在全艇军人大会上表扬了孙元明,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用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不久,155艇接受外训任务,抽出艇上的技术骨干,带训朝鲜潜艇兵,时间长达数月之久。外训接近尾声时,潜艇交由朝鲜人操练,我方人员“保驾”。孙元明带的朝鲜电工班长叫金光正。有一次出海训练,三舱下达了“速潜”的命令,金光正操作,孙元明在旁观察。金光正的动作比较熟练,但不小心把电罗经的按钮给碰了一下,断开了电源。孙元明及时发现这个情况,当即就给重新供电启动了电罗经。可电罗经有一个稳定的过程,重新启动后不能马上投入工作。潜艇在快速下潜,却一下失去了方向,三舱指挥员很着急,好在电罗经很快恢复功能,避免了险情。事后朝鲜机电长得知,这个险情是金光正制造的,便跑到四舱,“啪!”就给了金光正一记耳光,然后叽哩哇啦地把他训斥了一通。孙元明上前解释说,是金班长无意碰掉的,但无济于事。潜艇靠码头以后,这位电工班长还被关了禁闭。外训结束,朝鲜人要走了,孙元明知道金光正喜欢口琴,就买了一把口琴送给他,算是对他的精神安慰吧!金光正把自己平时用的钢笔送给孙元明做纪念。
在外训期间,孙元明又和朝鲜人开展了一次“一帮一、一对红”活动。
那个时期,可以回忆的内容太多太多。
2008年,我编辑老艇纪念册时,孙元明写了一篇文章《青春从这里启航》,记述了他在127、155、210度过的青春岁月。
青春从这里启航
孙元明
人上了年纪,就爱回忆“我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于是常常会拉上与自己谈得来的朋友,一起分享“年轻的时候”的时光。话匣子一开,往事就像丝线串起的珍珠,一个连着一个,一个比一个精彩。我这个已经抱上孙女的人,自然也不例外。
但我最爱讲,也是讲不完的,还是老127潜艇的故事。
那是四十年前,确切地说是1969年。当时潜艇士兵学校受到“文革”的冲击,停办了,我们这批兵结束新兵训练之后,没有经过潜艇士兵学校的专业培训,就直接上艇了。4月28日,我清楚地记得就是在这一天,我以潜艇电工兵的身份和其他13名新战友一起,被第一批分配到青岛五号码头,荣幸地成为127潜艇的一员。
上午9点多,我们乘着一辆大卡车,前往日夜期盼的潜艇部队。一进营区大门,就听到了远远传来的锣鼓声,心情猛然间被点燃。循声望去,沿着马路两旁有6栋二层楼房,远处1栋楼房门前,排列整齐的官兵,正敲锣打鼓夹道迎接我们的到来。
走近欢迎队伍的那一刻,我看着正中间门栏上高高悬挂的鲜红横幅——“热烈欢迎新战友”,听着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我的心激动得差点都要蹦出来。还没等回过神儿,老战士们已经抢过我身上的背包和手里提着的洗漱用具,拿到屋里去了,什么都有人帮着做,我只有傻愣着的份儿了……
我和东北籍大个子战士李万祥被分到了电工班,那时候除了艇长、政委、副艇长、副政委外,其他艇员都住在同一间大寝室里。一时间,我心中真的有了一种到家的感觉,而且是这样一个到处都充满着温暖的大家庭。
很快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走进饭堂,发现午饭意外的丰盛,无论是对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还是城市来的孩子来说,都是丰盛的,谁在家吃过这样的伙食啊!5菜一汤,荤素搭配,连主食都备了馒头和大米饭两种。餐桌是一个个大长条桌,一边能坐5个人。我第一次和班里的老兵一起,坐在大长桌前,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这些老兵是:刘锦和(班长)、孙振忠、陆根大、丁仕来、梁军、秦立荣等。
饭后,新兵们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好奇,迫不及待地想上艇去看看。我和大个子李万祥轮番缠着军士长请求上艇。军士长架不住我们的哀求,终于指派陆根大(我后来的师傅)带着我们俩上艇去了。不过前提是,要注意安全,并反复强调:只准看,不许动手!
在陆根大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停靠潜艇的浮码头。码头由南往北一字排开,最南边停靠水面舰艇,依次是装卸码头、交通艇码头、3号浮码头、2号浮码头、1号浮码头。3号浮码头正对着司令部,我们艇就停靠在这里,舷号:127。
那天天气很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海港,深蓝色的海水,在阳光照耀下碧波闪闪,各式各样的舰艇悠闲地停靠在这片壮阔的背景中。我们由浮码头登上停在左舷的127潜艇时,需经过一个很窄的、没有扶手的舷梯,透过舷梯木条之间的缝隙,深绿色的海水清晰可见,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当时我脑海一片空白,只想着能快点儿走过去,于是跟在李万祥后面,一步紧于一步地上了艇。这时我发现,要真正上艇还要通过舰桥边上一段更窄的甲板。港湾里有轮船驶过,荡起一层层波浪。潜艇在波浪的推动下轻轻地摇晃起来。我紧紧抓住舰桥的扶手,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舰尾走去。我知道,我很紧张。从艇尾升降口下到了7舱,呈现在眼前的是非常狭小的空间,到处是密密麻麻的机械、管路、阀门,只感觉嗡的一声,脑子就全乱了:眼前就是我们将来要驾驭的潜艇吗?这么复杂的潜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呀?
接下来从7舱一直走到1舱,哪是鱼雷舱,哪是电机舱,走马观花一趟下来,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倒是脑袋被狭窄的舱室碰起了好几个小包。可爱的李万祥,因为个子比我高,碰头的次数就更多了,每碰一次,我们都会默契的对望一下,然后忍住笑,继续防备着下次挨碰……
来到127艇的第一天很快就结束了,对于我而言,平凡却又特殊。夜里,我躺在床上,好久没睡着。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不能掉队!
我在艇上的战位是5-6-3-1(第5部门、第6战位、第3更、第1人)。于是,我从这个战位开始,与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共同驾驶着127潜艇,在大海深处留下了一条最美丽的航迹。
这期间有喜悦:第一次独立值更,让我一宿兴奋不已;也有苦涩:第一次挨批(值更时舱室进水),谁也没有反驳,没有借口,错了就是错了。从此,我将“严谨”刻进了我的生命轨迹,时刻牢记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条航迹中有快乐:第一次独自解决问题(我找出潜艇电池用电奇快的原因),由此激励自己遇事多加思考,为日后走上领导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期间更有骄傲:第一次紧急集合(兵贵神速),我终于更加自信,相信我可以超越自己……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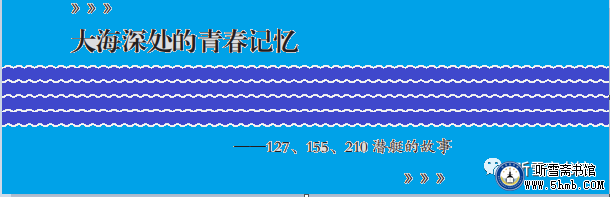
一转眼,昔日那个连走舷梯都紧张,一出海就晕船的懵懂少年,现在已经当上爷爷了。不知道曾经并肩奋战的战友们,是不是也如我这般,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讲着永远都不会厌倦的127潜艇的故事。
踩一下[0]

顶一下[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