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友达(1957.3~),湖南省常德市人。1976年1月入伍,曾任210潜艇舰务兵、舰务班长;1984年到潜艇支队政治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1985年起,先后到北海舰队政治部创作室、海军政治部《水兵文艺》编辑部从事创作、编辑工作。1988年转业,曾任常德市电视台记者、《桃花源》文学杂志社编辑;1994年初调中共常德市委工作,先后任市委副书记秘书、常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王友达他们那批1976年兵经过专业培训分到艇上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到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了,只因要参加原计划9月份的远航,没有走。9月份毛主席逝世,任务推迟;10月份粉碎“四人帮”,任务取消,我就到支队政治部报到去了。对王友达他们那批刚上艇的新兵基本没什么印象。
一个月后,全国政治形势稳定,上级命令远航任务继续执行,我便回艇参加远航,又当了一个月的轮机班长。在这次远航中,艇上搞了一次水下晚会,这次晚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舰务班的新兵演出了一个“湖北渔鼓”。水下晚会的特点是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不知他用什么当渔鼓,也听不懂他哼哼呀呀唱的是什么,但是让我记住了那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新兵的名字——王友达。
远航归来,我继续回政治部当干事。一年半后,我被调到舰队政治部创作组当创作员。这期间,我经常回老艇转转,与王友达也会碰面。这时我还不知道王友达也喜欢业余写作。后来他送了几篇他写的东西给我看,基础不错,问题不少,我给他简单提了几条意见,他表示回去再写。不久他又送来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写潜艇兵水下生活的文章,我给他修改了一下,换了个题目,并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把稿子抄一下,直接寄给《人民海军》报的副刊编辑林道远。不久,文章在海军报上发表了,这就是他的处女作《水下半小时》。据王友达回忆,是发表在1981年6月4日的《人民海军》报《水兵》副刊上。
我是在艇上当水兵时开始业余写作的,我深知业余写作的艰难。每天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全艇住在一个大寝室里,可以用来个人支配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只能利用在艇上值更的时间写写。当然还要把本职工作干好,不然人家会说你“不务正业”。我提醒他要处理好业余写作和本职工作的关系,同时还要和大家处理好关系,不然就会影响自己的生存环境。
后来我了解到,他把这些关系都处理得很好,大家对他的反映不错。
渐渐地,王友达的“野心”也大起来,不满足于写小文章,开始学习写小说,而且一出手就是中篇小说。1984年,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拿给我看,正好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在江西上饶举办业余作者学习班,我就推荐他和另外一名舰队的女作者去参加了。据说那次海军各大单位去了不少人,最后只有两个作者发表了作品,这两个人都是我推荐的,其中就包括王友达。他的中篇小说《潜艇艇长》发表在1985年的《清明》杂志上。当时能够发表中篇小说的海军业余作者不多,王友达成为海军业余作者中的佼佼者之一。从此,也奠定了他在海军业余作者中的地位,他长时间在舰队和海军机关帮助工作,也说明了他的实力。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炼在个人。我只是在他初学写作的时候,用我的经验和体会给予他指导,并给他提供了一些机会,后来的事情就完全靠他自己去努力了。他转业到地方后,当过电视台记者和文学杂志编辑,如果不是被市委机关选去给领导当秘书,也许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绩会更大一些。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于作家来说,一切生活经历都不会浪费,都将成为创作的素材。也许有一天,他会写出精彩的官场小说,因为不会有什么人比领导秘书更熟悉官场了。
王友达是个爱交朋友、办事热心的人,他在给领导当秘书那些年,交了不少朋友。这些朋友也是一种资源和财富。
2008年,我编辑老艇纪念册时,他帮助做了很多工作,曾专门陪我去温州见纪念册的策划人之一陈献彩,在印刷费较高的情况下,他还赞助了5000元。
在那本纪念册中,他写了一篇文章《“渔鼓”催我奋进》,记述了他在210艇经历的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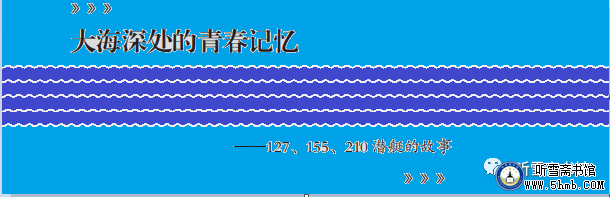
记不得是1975年的哪一天,父亲郑重地告诉我:友达,公社今年有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公社书记准备推荐你上大学。那会儿,我已经当了一年半的“赤脚老师”,上大学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可我却没有丝毫的犹豫,回答父亲说:不,我要去当兵!当兵,那时成了我惟一的追求。终于,我的“兵梦”实现了。
1976年初,我和一群新兵乘了几天的“闷罐车”,迎着刺骨的寒风,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成为一名光荣的潜艇兵,成为海军先进艇——210潜艇的一员。从210潜艇鸣笛起航,开始了我的人生新航程。也许是我的运气,不久,我在众多的新上艇的水兵中被挑选去参加了一次30昼夜的远航。
我在我的一部中篇小说集的后记里这样写道:“我曾到茫茫深海的台风中心跳过‘迪斯科’,见几层楼房高的波涛气势汹汹滚辗过来时,面不改色……当然心儿还是要跳的。在那像罐头筒似的密封的与世隔绝的神秘兮兮的潜艇舱室里,官兵们一块压缩饼干轮着啃,一瓶水果罐头分着吃;汗往一起淌,劲往一处使;心儿贴心儿,战友是兄弟。这种纯朴的友情,真诚的关心,今天看来是何等宝贵。每每回想起就有几多激动几多留念!正是这般生活赐予作者创作的源泉。”
如今,1976年的远航已过去了32载,我惜别海军也有整整20年了。我不知道,现在海军是否创建了“远航文化”(文学)。正是1976年的远航所产生的“远航文化”(文学),给予了我生活的寄托、精神的营养和工作的快乐,将紧张危险、枯燥泛味的潜艇生活赋予了青春的活力与战友间的凝聚力。
水下晚会,是我们独特的水下文化娱乐生活之一。我是湖南兵,在楚文化发源地长大,家乡有个曲目叫“渔鼓”,就是用直径十厘米左右,长度不过两尺的竹筒,一端蒙上蛇皮,然后用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三根指头敲打蛇皮面,发出咚咚的声响,嘴里念念有词,便就叫打“渔鼓筒”,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那时在水下,找不到这种道具,就敲打着罐头筒,唱起了“渔鼓”:手敲渔鼓心激荡,我乘“蓝鲸”来远航;水下世界真奇妙,唱起渔鼓夸班长……
我是舰务兵,班长叫陈国校,我赞的就是他的老黄牛精神。虽时过30余年,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这个节目受到了大家称赞,老兵们经常要我哼“渔鼓”。正是这次远航的水下晚会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经常给《水下战报》投稿。还有幸结识了随艇一道远航的支队政治部宣传干事李忠效,他曾是210艇的轮机军士长,写得一手好诗和散文,读他的文章和经他辅导,受益匪浅。
如今回想起来,应该说我作为新艇员就随艇远航还是算比较优秀的,更主要的是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锻炼。我不怎么晕船,为人忠厚,热爱学习,尊重老兵,因此大家都喜欢我。潜艇远航淡水紧张,每人每天只发一茶缸淡水。带我的老兵苏连文有脚气,他在三舱底几乎每天都洗脚,我经常把我的那份淡水贡献给他,远航30天,我一次脚也没洗过。那时我的战位在三舱底,就负责管淡水,却从来都没使用“特权”,私下多用一滴水。有时脚底实在不舒服了,就会在老兵洗脚时从他的脚盆里沾湿抹布擦擦脚了之。潜艇远航生活很苦,今天想起来却感到特别有趣,那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啊!
因为我不怎么晕船,就参加了由政委王学芳组织的送温暖小组。我那时长得比较胖,又是一副娃娃脸,还真有点讨人喜欢,有很多老兵叫我小胖子。我这送温暖小组的任务就是在同志们晕船时送上一杯水,捶上一阵背,打扫一下呕吐物等。那时觉得这个任务很光荣,为“兵”服务,首长夸奖,真自豪真骄傲啊!每当听到“小胖子给我倒杯水来”,“小胖子,哼段渔鼓”等等,我心里就喜滋滋、甜美美的。每当休更时,我就蜷缩在哪个机械仪器的旮旯里,开始为《水下战报》写稿。既写表扬稿,也写小散文、诗歌什么的。30天的远航生活结束后,我的长进真不小。
说实在的,尽管后来我又参加过远航,也干过同样的差事,但惟有1976年的远航,刻骨铭心,每每回想起来,至今都叫我心情激动难平。远航回来不久,我就在“5战1”独立工作了。我把铜器擦得锃亮,把机械设备保养得完好,经常得到鱼水雷部门长于水洋的表扬。他骂人可凶了,舱室里的人常遭他批评,可我至今仍100%地记得他没骂过我。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关怀备至。记得有一次从一舱升降口装鱼雷时,我的手指卡在链条和齿轮间,被绞车压破了,疼得几乎晕了过去,他及时给我安慰和救治,至今都令我感动。
工作之余,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梦想在文学的殿堂里创造自己的辉煌。那时候这叫“不务正业”,怕被首长发现,常常自己拿着小马扎和一个硬夹本,躲到码头的礁石缝中,坐在小马扎上,将硬夹本放在膝盖上进行写作。码头鱼水雷检修所旁有一个汽车库,在停放卡车的车尾有一道间隙,也是我时常光顾的创作场地。特别是在夏天,不知养活了几多蚊子。在深秋和冬天,码头的天气实在太冷了,只能趴在寝室的床上写作(我喜欢睡上铺,脚踩着蹬子),有首长来到我的床前,问我干什么,我就很平静地回答说:写家信。一下就蒙过去了。只有当时任潜艇副政委的王中才知道我的秘密,知道我在向作家之路奋进,同时也得到了他的帮助和鼓励。至今,我从心底里感谢他。这其中,李忠效同志给了我莫大的帮助,那时他调到舰队政治部工作,我常拿着自己的习作到政治部去拜他为师,请他斧正。于是,有了我后来的创作成就:像散文《水下半小时》、《水下赏月》;小说《听》、《潜越》等等。
人的命运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有了1976年随210潜艇远航的经历,那神秘的水下世界,赋予了我创作的激情、创作的欲望和创作的灵感。掐指算来,我这些年一共发表了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文学作品100余万字,出版了中篇小说集《海祭》、报告文学集《走向辉煌》等;参与编剧或摄制的电视剧有:《紧急下潜》、《海星》、《雄关》等。满以为我会在文学之路上一直走下去,但最终还是没能实现我的专业作家之梦。
1988年,我转业回到阔别12年的家乡——常德。海军作家杨肇林曾经赞誉常德:这是一片有着丰厚蕴藉的沃土,有屈原行吟过的沅江,有陶渊明寄托理想的桃花源,有刘禹锡留连十载的古朗州;沈从文从这里走出“边城”,丁玲从这里发出“莎菲女士”的呐喊。如今,我从一名潜艇水兵(战友们也常把“水兵作家”的帽子戴在我头上),成长为地方的一名小小的处级领导干部。尽管工作的环境变了,任务的性质变了,服务的对象变了,但心还是那颗潜艇水兵的心。我永远铭记着1976年的远航。“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人生一世,其最大乐趣莫过于做成想做的事情,但也要寻条鞭子时刻抽打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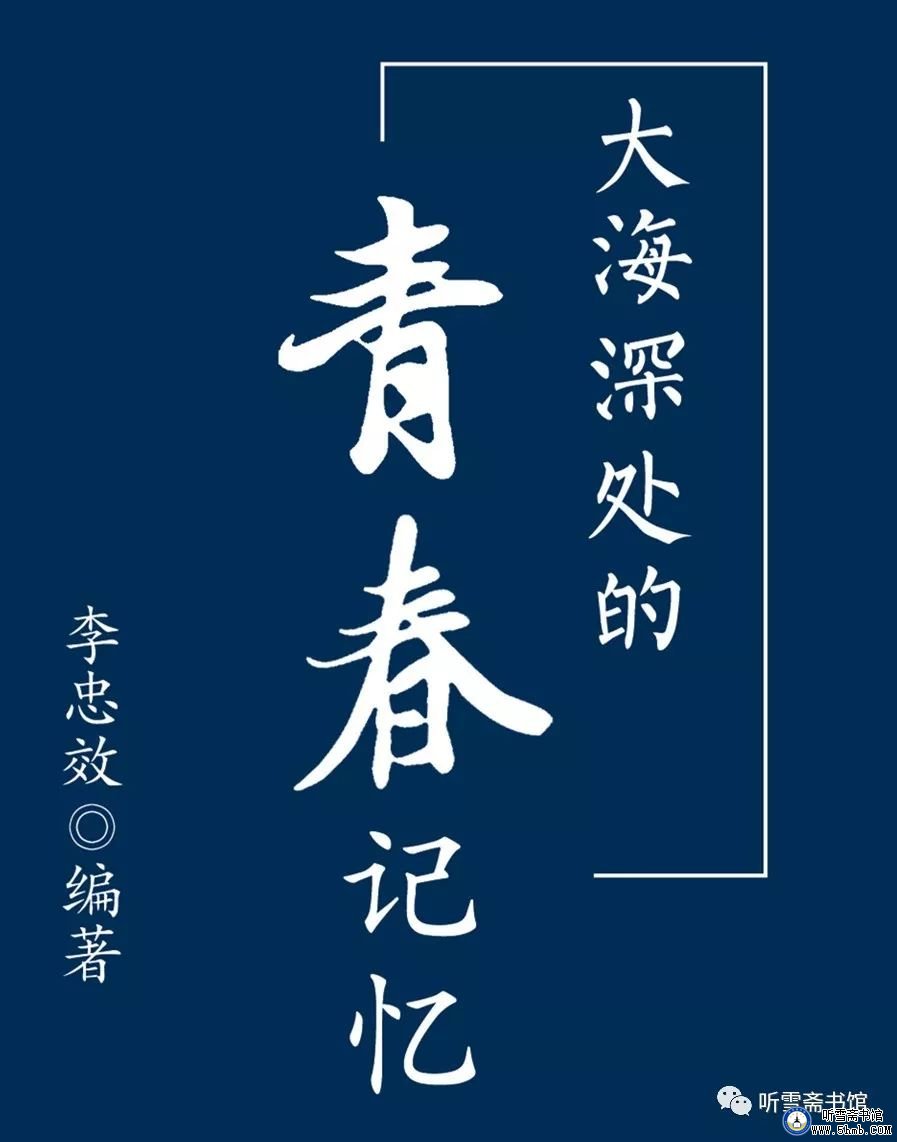
本网站近期连载海军作家李忠效编著的纪实文学

李忠效,笔名:钟笑。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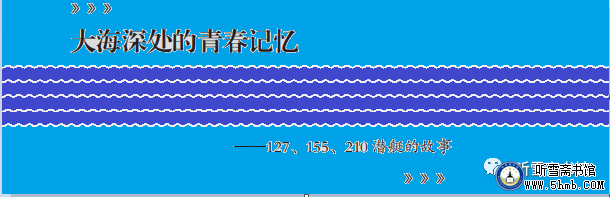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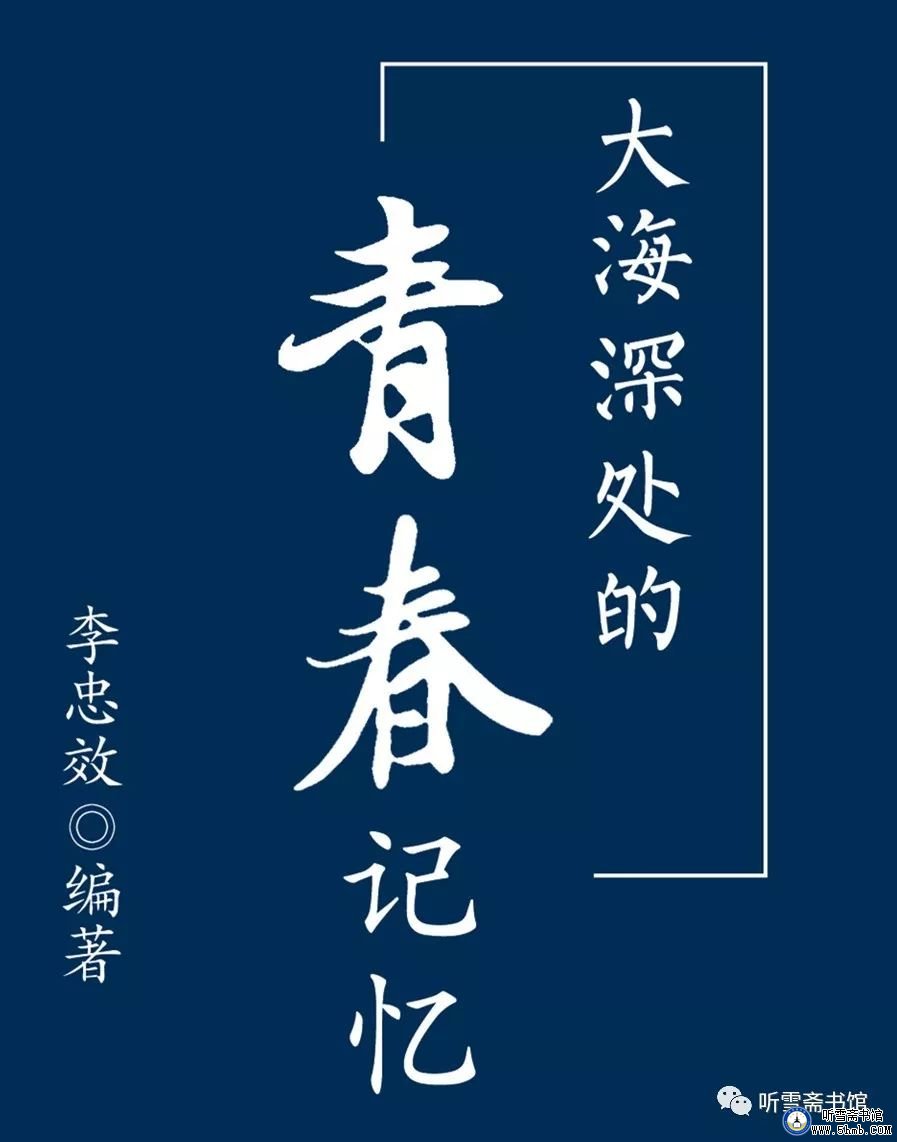


顶一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