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机电部门 电工班 《大海深处的青春记忆》(23)
友情与乡情
当了潜艇艇员我才知道,同样是战士,海军和陆军是那样的不同。我说的不是海上和陆上的不同,而是更深层次的不同,只有干过两个军种的人才能说出这种不同来。
陆军以连排为单位,可以利用地形、地物作掩护,进行单兵作战,打不下去了,可以转移或隐蔽起来。海军就不行,一条潜艇就是一个团级单位,全艇各战位要协同完成一系列动作,集中到最后一个战位,用鱼雷去打击敌人。打完后在海面上你无处躲藏,到水下敌人也可以用声纳追踪你。
陆军作战单元可大可小,可集中可分散,灵活得多。海军不行,全艇人员都在一个活动的容器内,一出海就是10天半个月的,有远航任务时,要在海上泡一个来月。在水下全靠再生药板改变空气质量,再生药板放出的热量可达40°C以上,热得够呛,热得难熬。到空气筒航行时,要给蓄电池充电,电工兵值更要测比重,下到电池舱,里面的气味简直要熏死人。到上浮半潜时,一桶桶的舱底污水和生活垃圾要倒掉,拎桶负重爬升降口,几个来回就要累得半死。一出海,吃又吃不下,睡也睡不好,如果远航一个月,终日不见阳光,回来以后个个脸色煞白,都像是“白骨精”。当你钻出升降口,拖着沉重的步子登上码头,连回寝室也要走一步晃三晃,可谓筋疲力尽,虚弱之极。潜艇兵就是这样工作、生活、战斗在一起,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一个生命都联系在一起,每一次出海都可能与亲人永远“再见”。
这样的战友感情,是整体的,血浓于水的,是经历了大风大浪、狂风暴雨、晕船呕吐、艰难险阻的生死考验而磨合铸就的,要比其它军种来得更加强烈。正因如此,潜艇艇员的战友情谊,要显得更加深厚和牢固,远久不逝,越长越“醇”。至今,我到青岛、大连、南京等地出差,总忘不了去会会老战友。35年过去了,我见面就能叫出他们名字,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心中的激动就如大海一样汹涌,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种海军情结,艇员友谊,肯定会比陆军团队来得深,来得切。现在搞这个老艇纪念册,一定会渗透着老艇官兵的深切思念和永恒的回忆。
我们艇长张连忠是经历解放战争的老兵,经过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解放后他一直在31军,驻守漳州厦门一线。我参军后在28军,驻守蒲田泉州一线,两军是联防部队,共同坚守在对台作战的最前线,阵地前方就是金门、马祖、大担、二担。我的人生经历跟艇长不能比,也不敢比,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从陆军调到了海军,又是山东老乡,所以,见到艇长后就格外的亲切。我刚上艇,第一次见到这个山东老乡,看到他个子不高,皮肤黝黑,并不觉得有什么与众不同。然而,他一开口,操着胶东口音说:欢迎你们上艇!嘿,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嗓门,一下就震动了我——到底是陆军过来的,跟蒋匪军拼过刺刀,冲啊!杀……像个陆军的老兵!当他用虎钳般的手握着我的手上下摆动时,我顿时感到了山东小个子的力量。最让人难以忘怀的,还是艇长的那双虎瞪瞪的浓眉大眼。他一说话,一亮眼,“精、气、神”就喷发出来了,让人感到中国军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气和勇气。
在以后的工作、学习、训练、执勤中,艇长时时处处在培养和锤炼着我这个陆军来的小老乡,见到我总是笑呵呵的,这在一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心里产生了浓浓的乡情。其实艇长就是个表面严厉而内心特别善良的前辈和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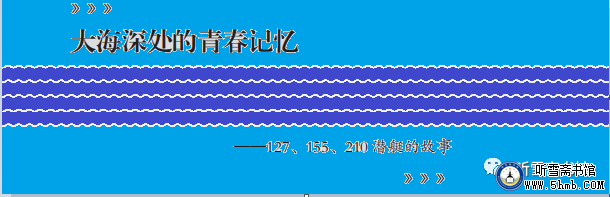
海军与陆军
上艇不久,我们这批陆军来的同志中有一部分人提出要回陆军老部队去。我了解到他们不是怕苦怕累,不是生活不习惯,更不是不愿干海军,他们主要是看不惯码头上、艇上那种“搞来搞去,斗来斗去”的风气。这种风气在陆军野战部队是无法想象的。陆军的作风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哪有这种“艇上派,艇下派,艇长派,政委派”的争斗呢?这样把自己搞乱了,怎么能应付外来入侵呢?但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的影响和破坏,在海军内部的斗争随处可见,不足为奇。当陆军的同志到我这里来联络请调一事时,我明确告诉他们自己不想回去了,在哪里都是当兵,都是保家卫国。我告诉他们,咱们127艇很好,很团结,没有你们讲的“这派那派”的情况,在这里我感到与陆军生活一个样,一起打球,一起唱歌,一起学习,一起出海,就像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特别是我们在寝室里打乒乓球的时候,艇长总是一个人坐在床头笑呵呵的看着,看到打得好时,还不停的叫:“好球!好球!”我们这帮打球的战士,都喜欢叫艇长观战,一打球就叫“艇长,打球了,打球了!”艇长听见了,笑眯眯地就从艇部走出来说:“好!开始,开始。”艇长喜欢体育,更支持我们强身健体。在他的关心之下,我艇的乒乓球、篮球活动开展得很活跃。特别是乒乓球,还得了支队的冠军。你说生活在这样团结友爱的气氛中,我怎么还想回陆军呢?(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
踩一下[0]

顶一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