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6)
随后,我们姐妹俩把要去上海读书的想法告诉了母亲,并强调说,刘老师和蔡老师都表示支持。开明的母亲知道,要想改变女儿的命运,也只能让她们出去闯一闯了。既然女儿已经下了决心,就随她们去吧。
第二天,母亲找出自己陪嫁的首饰和还值几个钱的衣物拿去变卖,为女儿准备盘缠。
我的二哥叫沈勤,在扬州盐务稽核所供职。他与我们两个妹妹感情很好,听说我们要去上海求学,便积极支持。他帮沈珉办了离婚手续,还赞助了我们俩一些钱。就这样,我们姐妹俩在老师和亲人的支持下, 挣脱了封建的枷锁,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新生活。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鸡叫头遍,天还没亮,泰兴县城的北门大街沈家大院的宅门,走出我们姐妹俩——20岁的姐姐和17 岁的我。我们一人挎一个蓝底白花的包袱, 我手里还提了一个小巧的皮箱。外人一看便知,我们是要出远门了。母亲在小伙计陈三的搀扶下跟在后面,出来为两个女儿送行。她虽然是小脚,但走起路来脚步却坚实有力,她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克制而平静,显然她不想让远行的女儿还没启程就哭哭啼啼。

★23岁的沈伊娜(沈珉),1936年摄于上海
我和姐姐站在大门口,回头看看沈家大院,当年昌盛时的模样还依稀可见,只是大伯父沈文瀚的红轿子不在了,大伯父独用的小洋楼书房也破旧不堪了。黑漆的大门上油漆已经剥落,门上的铁环生了锈,连墙砖的缝隙也长出了杂草,显出没落封建大家庭的衰败景象。
母亲事先雇好了鸡公车,这是一种既能坐人又能载物的独轮车,也是那个年代泰兴人出远门常用的交通工具。
当时母亲才四十多岁,可是已经守寡多年。她不辞劳苦,好不容易将儿女们抚养成人,而今又都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她。两年前她刚送儿子沈勤去扬州谋生,现在又要送两个女儿到上海求学,她们的前途将会怎样,谁也不清楚。此刻,只有做儿女的才理解母亲的心情。
我和姐姐在陈三的帮助下,每人抱着一个小包袱上了鸡公车,小皮箱放在中间,两人各坐一侧,鸡公车就吱吱呀呀地上路了。母亲站在门口默默地向我们招手,姐姐又哭了。我没有哭,我轻轻提醒姐姐道:“别哭,娘会难受的。”
沈珉马上抹去了眼泪。她不想让娘为我们伤心。
我们姐妹俩回头再看一眼娘, 再看一眼生于斯长于斯的沈家老宅,此次别离,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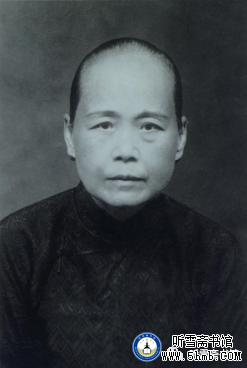
★沈安娜母杨淑怀,摄于1950年
母亲迈开尖尖的小脚,跌跌撞撞地向前跑了几步。她想再看一看,送一送即将远去的女儿。可她赶不上鸡公车夫的大步,只好停下来,站住了。她无奈地向女儿挥了挥手。她心里明白:不走,又有什么出路呢?还是让她们自己去闯吧!
随着鸡公车吱吱呀呀的响声,
我们看见母亲和沈家大宅门在浓雾中一点点变得模糊起来。最后看见母亲放下了轻轻摇晃的右手,与左手交叉着垂在身前,像一尊雕像立在那里。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这个形象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泰兴县有着千年历史。它位于江苏中部,东接如皋,西临长江,南界靖江,北依姜堰,原为海陵县地。南唐烈祖升元元年(公元937年)因升海陵为泰州,乃析海陵南境五乡设立泰兴县,即随泰州兴起之意。20世纪30年代, 由于长年战乱,官匪勾结,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泰兴和苏北的一些小城镇一样,百业凋敝,农村的自然经济破产,民不聊生。为了躲避战乱和破产带来的危机,大批难民和破产农民盲目涌向城镇,以向命运做一次抗争。可是他们一贫如洗,无衣无食,贫病交加,饥寒交迫,往往于途中便撒手人寰。我们姐妹俩见沿途哀鸿遍野,路有饿殍,顿生恻隐之心。对这些遭受灾难的同胞, 我们寄予无限的同情,对昏庸无能的当局,心怀极大的悲愤。(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
踩一下[0]

顶一下[0]